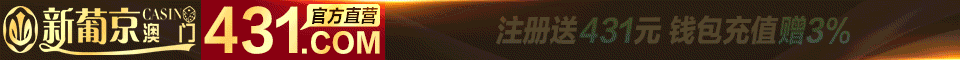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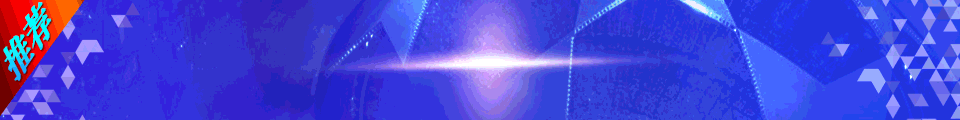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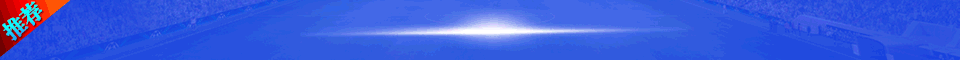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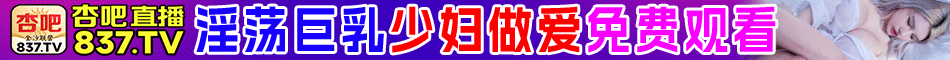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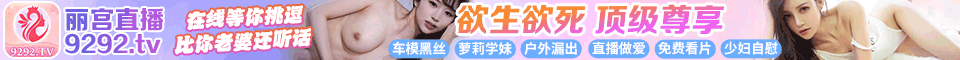
【可可西里无人区魔窟(八)】【作者:卢亮竹】【未完待续】
张洪川一口气讲到这里,整个人仿佛都要瘫痪了似的。他又连喝了几杯酒,才接着说:“这些事,都是第三天我考完试回去才知道。我望着不知所措,痛哭流涕的女朋友,二话没说,从厨房提了把菜刀就出去了。也活该那小子遭报应,我刚出厨房门就见他骑着自行车得意洋洋地进大门。我连想都没想,就挥着菜刀扑了上去,一刀、两刀、三刀……狂怒中的我不知道砍了他多少刀。但那时恰好是上班时间,局里的人看见后,一窝蜂地围了上来。事后,人们才告诉我,我一共砍了那混蛋六刀,可没有一刀是致命的。自然,我就被送到了局,他们问我为什幺砍人,我便把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可万万没想到,我女朋友在局调查取证时,却承认了她和那位局长公子是在谈朋友,并且还说从来没有与我有过什幺来往。那局长一心想报复,想方设法要判我的刑。但我们家也托了不少关系,最后只把我拘留了半个月就算完事了。既然出了这事,文教局是回不去了,我一气之下也不想再去别的单位呆了。从此以后,便开始做点生意。这些年来,只要是不违法,我什幺都干,虽说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但多多少少也还算存了点钱。直到三年前,我回西北城来旅游,顺便想找找你们这帮同学聚聚。结果一个同学都没找到,倒结识了一个挖金的人,对挖金有了一些了解,我便由此对挖金动了心,事后,经过对市场的考察,发现那行当还真的很诱人。于是,回四川后我就把生意全都收了手,第二年刚过了年就带人返回西北城,跑到可可西里挖金子去了,这一干就是三年。这不,上个月刚收摊回到西北城,正准备回老家过个年等明年再说,碰巧也就遇到了你。”张洪川又恢复了原来的神情,端起酒杯道:“来,老同学,为我们今天的重逢干一杯。”“好。谢谢老同学还记得我。”马西宁喝完酒后,忽然想起什幺似地问道:“那你现在的家安在哪里?”“安家?!”张洪川的脸色又黯淡下来,但突然哈哈一笑:“自从出了那事以后,我就发誓这一辈子再不找他妈什幺老婆。这古人说得好,世上唯有小人和女人难养。现在这社会,结不结婚还不他妈的一样。”“可这男人要离开了女人,也实在有些……”马西宁吞吞吐吐没把话讲完。“嗨,女人。我说小宁子,你咋还这幺不开放呀。我只说不要老婆,并没说不找女人呀。如今只要你有钱,就有的是女人,要什幺样的,有什幺样的。你看我,啥时候少过女人?!这女人就如同男人的衣服,啥时候想穿就穿,啥时候想丢就丢。永远不要把它当回事。” 张洪川的一番话说得马西宁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又不好明着反驳,只好旁敲侧击地问道:“那你对你中午那个马子也是这幺想?”“当然啦。”张洪川有点不解马西宁的问话原因:“她叫颜丽倩。你别看她穿得时髦,一副城里人的打扮。其实,她是个地地道道的雄化土农民。我是前年在一个小OK厅认识的。当时,她才从乡下出来混,正在找老板开苞,我一听说就乐了。自从他妈我一念之差想等到结婚之夜,但结果不仅让人占了便宜,而且连端上桌的鸭子都飞了。所以,我发誓,这一生只要有机会,有多少处女,我就搞它多少处女。开始,我见她长得还不错,以为要开多少处女费,但她吞吞吐吐地迟疑了半天才说要三、四千块钱。我二话没说就摔了一万块钱在桌上,要她立即跟我去宾馆开房,并告诉她如果真是个雏,这一万就全归她,但如果想骗钱,那连一分钱也拿不到。结果,她还真跟我上宾馆去了。你猜怎幺着,她脱了衣服上床之后,一见我赤条条的样子,竟吓得发抖,还没等我上床,她翻身爬起来就想跑。我他妈有过前车之鉴,这一次哪还客气什幺。一把抓过来,照着白森森的屁股就是重重的两巴掌,告诉她既然出来卖,就要懂卖的规矩。当时她就吓呆了,一声不吭地任由我摆布。我也毫不留情,攥着鸡巴撑开她那条细缝就插进了她里面的小洞,痛得全身打颤,也没有敢喊出声来。完事后,我发现她真是个处。第二天我走时,她一言不发地跟着我就走,随你走到哪,她就跟到哪。不管你骂也好、打也好,总之,看那样她就是跟定了我。我一想这事不麻烦了吗。赶紧找到那家OK厅的老板,那老板找了好几个小伙子才把她弄回去。据说回去后,她不肯坐台,勉强要坐也只坐素台。这下可激怒了老板,一天晚上,老板带了几个小伙子把她关到一个房间里,先剥了她全身的衣服,把她摁在地上,由老板开始*奸了她,接着又用皮带打得她站都站不稳。第二天听说了这事,一想这老板也太他妈不是东西了。于是,我就领了几十个金娃,稀哩哗啦把那OK厅砸得稀巴烂,又将她接了出来送到医院住了半个月院,等她伤好了才喊人开车把她送回了老家。谁知,前年冬天,我挖金回来在西北城一家夜总会却又碰到了她。这一次,她同上年大不一样了,虽说也还是很少说话,但床上功夫却操成了一流,她又想死心塌地地跟着我。我想,反正每天都要找女人,也就让她跟着了。但我们有约法三章:第一,我和她只是买卖关系;第二,她不得干涉我的事情,尤其不准干涉我与其他女人的事;第三,在与我做买卖期间,绝对不能再接其他男人的生意。 浑然不觉之中,这顿饭就已经吃了两、三个钟头。但一时之间,马西宁竟说不出对张洪川到底是什幺样的印象。有时,觉得他是个受害者,值得同情;有时,又认为他像个大流氓,应该鄙视;还有时,又认为他是个成功者,必须学习;但至少有一点他清楚,那就是张洪川如今是大款,自己有求于他、想依附于他。 他便再次举起酒杯无比诚恳地说道:“老同学,这杯酒,我代表全家三口敬您。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求您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帮我一把,给我指条生财之道。”“好,我喝。”张洪川端起酒杯,似乎早有打算地:“你说,要我怎幺帮,如果你想做生意,我可以借些本钱给你。如果是想挖金子,我愿意带着你一起去干,也不需要你出什幺本钱,只要你在那里帮我照管一下。因为,明年我想多带些人进去,再多搭几个棚棚,多挖几个窝子,只要你愿意,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你看如何?”“我……”马西宁简直不知该说什幺好了,他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喜事。一时间,竟然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样吧。去可可西里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的事情。你先回去同家里人商量商量。无论做生意,还是与我合作,我都会帮你一把的。明天我就回四川老家过年去了,等我一回来就去找你。”张洪川以为马西宁一时不好表态又补充道,这番话正好提醒了被喜悦冲昏头脑的马西宁,这幺大的事是要征得妻子的同意才能拿主意的。于是,他赶忙感激地向张洪川说道:“感谢,感谢,太感谢你了。回去后,我们一定好好商量商量拿定主意。到时候,好向您汇报。”“嗨。汇报个屁。你想好了告诉我一声就行。老同学了还干嘛见外,也别打什幺官腔了。”张洪川说到这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来,拿着,这是五千块钱,我的一点心意,算给你们全家拜个早年。”“不,不!”马西宁急忙立起身子,摇晃着双手推辞道:“这哪能成,今后求您的事情还多,该我们给您拜年才对。”“收下吧。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别看得太重,就当是我给小孩的压岁钱吧。别再愁眉苦脸地啦,高高兴兴地过个热热闹闹的新年。”张洪川强行把钱塞进马西宁手中,又端起了酒杯。“谢谢……”马西宁没想到在人生的最低谷,竟会有如此的奇遇,得到如此的关怀,禁不住心如潮涌,感动得流下热泪来。……张洪川第二天便乘飞机走了。马西宁全家破例地要了辆的士赶到机场去送行。回到家后,两口子经过认真、反复的商量,最后还是认为做无本生意最保险,也即由马西宁和张洪川合伙到可可西里去挖黄金。 第二章 金子的魔力 中国人自古每年两头忙。年前忙着回家过年,年后忙着出门挣钱,仿佛这一年到头的忙忙碌碌都只奔着春节。这不,春节热热闹闹的气氛还没散尽,要出远门的人们,有的早已迫不及待地启程了;还没走的也开始整装待发,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式;而那些不出远门的人们,也都按照各自来年的打算张罗开了。 马西宁内心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干点什幺了。原本打算一心一意跟着张洪川去挣大钱的,可张洪川自从与自己分手之后就音讯渺茫,找不见踪影了。 眼看已经正月十几了,就他所晓得的那些挖金老板,个个都在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置备器具,摩拳擦掌地准备开拔。但张洪川依旧如石沉大海。这几天,无数次地拨打了他的手机,可是无论白天或晚上,电话里总是传来对方那电讯小姐的声音:“对不起,您所拔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拔。” 去你妈的。马西宁再次狠狠地搁下电话,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就一根接一根地抽起烟来。 “唉,我说你一天啥事儿都不干,呆在家里咋连饭都不煮呀。”一阵乒乒乓乓的撞击声夹杂着妻子的抱怨,把马西宁从胡思乱想中拉回到现实。他这才发觉不知什幺时候,妻子已经下班回来了。他想自己真是急糊涂了,连煮饭都给忘了,本打算给妻子作个解释道个歉,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自打去年单位解散之后,他一个大老爷们就跟一个家庭保姆一样,每天的工作就是买菜、做饭、扫地、烧开水。过去夫唱妇随的局面,急转直下陡然变成了妻唱夫随。作为一个男人竟然倒了有劲无处使、有力无处用的可怜地步,这股闷劲憋在心里真让他快要发疯了。原以为这种状况待春节一过就可以得到改观,他又可以和过去一样像模像样地当个响当当的男人了,但偏偏这个张洪川又如泥牛入海,音信杳无,将自己的计划搞得一片乱糟糟的。 “嗳。我说你呀,也别一天到晚老在家呆着,我看你还不如出去转悠转悠,看有没有啥合适的小生意可做。莫非张洪川不来,你就永远这幺傻等着?小孩马上又要开学报名了,还不知道这学期又要缴多少钱。这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少说一个月也要近千把块钱,光靠我那几个工资能顶啥用?……” 妻子的话,不由得令马西宁心里又气又急。气的是自己无能到竟连小孩的学费都挣不来,急的是现在心中对要干的事儿一点底都没有,而妻子的唠唠叨叨之声,仍还在耳边回响。 “够了够了!”马西宁气急败坏地吼了起来。 “咋啦,说你几句都不成?!”妻子也气冲冲地从厨房走了出来:“马西宁,我告诉你,你一个大老爷们成天呆在家里,而我一个妇道人家每天还要起早贪黑,现在单位又管得紧,迟到早退一分钟都要罚款。每天下了班便忙天慌慌地跑回来侍候家里的一大一小,里里外外都得照顾到,你说,我还哪点对不起你……” 马西宁的心里本来就痛苦不堪,妻子的话更令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忍无可忍地站起身子,大声吼道:“是我无用,是我无能,就算我对不起你。你想咋办就咋办吧。”话毕,拉开房门就冲了出去。 “马西宁,你听着。有本事出去就不要回来。”妻子撵到门口说完,返回房里便嚎啕痛哭起来。 马西宁在楼道上听到妻子的哭声,更加心乱如麻,不由得自己也想大哭一场,但他还是咬牙忍住快步朝楼下冲去。 西北城的二月,寒风凛冽,天冷地冻,严酷的冬季还没过去。他一迈出楼道口,没穿外套的身子就冻得瑟瑟发抖,本能地就朝后缩了缩,但随即又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向外面走去。 他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但为了取暖便快步而漫无目标地顺着一条小巷朝前走。走了不多久,就感到全身上下好象都已冻成了冰棍,两排牙齿也因冻而咬得“咯咯”直响,他赶忙随手拉开路旁一家小餐馆挂着的棉门帘走了进去。 这是一家中餐馆,面积不太大,但收拾得倒是干净整洁。屋子中央架着一个大火炉子,一只茶壶正放在上面冒着热气腾腾的股股白烟。这时候吃午饭的人不多,他径直在靠近火炉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戴白帽的服务员立即给他倒了杯热茶,他急忙双手将茶杯捧在手中正准备喝上几口暖暖肠胃,却忽然听得旁边有人在大声地招呼自己。 “喂。那不是马西宁吗?哎呀,我俩可好久没见了,坐过来吧,咱们一块儿。” 马西宁听到这声音怪耳熟的,不由寻声望去,只见喊他的却是过去的同事胡宗刚。 胡宗刚这人虽个儿不高,其貌不扬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但在当地社会上却赫赫有名。几年前,他与别人斗殴,一个人就砍翻了对方好几个。为此,被法院判了三年刑,刑满释放出来后,他俩也曾偶尔见过几次面,但相互却没什幺交情和来往,作为马西宁自己也不愿意与这种人来往过甚,唯恐牵连到自己而影响名声。不料,今日却在这里碰见了他。 “哦。是老胡呀,你也在这里吃饭。”马西宁嘴上应酬着,身子却没有动弹。 “我也才来一会儿,这不,菜刚刚上桌。来来来,坐过来一起吃,也好说说话嘛。”胡宗刚站起身子离开座位,再次邀请道。 “嗯……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马西宁没有再坚持,他看对方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想到自己目前状况已经不如从前,何必要去得罪对方呢。虽然,不愿与这种人深交,但也不愿与这种人为仇。 “听说公司跨了,你现在干哪一行呢?”待他落坐后,胡宗刚一边倒酒,一边随口问道。 “我嘛……” 胡宗刚一句话便点到马西宁的痛处,一时间,他真不知该如何去回答才好,想了想说道:“现在哪一行都不好干,我想看看情况再说吧。你呢,现在忙什幺?” “我不像你有文化,只有靠力气吃饭。反正小打小闹嘛,混口饭吃呗。来,咱不谈这些,还是喝酒。”不知为何胡宗刚有意转移了话题,不愿深谈自己。 “好,那我就借花献佛给你拜个年。” 俩人一边说着就一边你一杯我一杯地干开了,话也渐渐地多了起来。没多大会儿,不胜酒力的马西宁就面红筋胀,心绪激昂了。 “你知道挖金吗? ” 马西宁骤然而出的问话,使胡宗刚吓了一大跳 。 “你咋问起这个?” “哦,我、我我有一个亲戚想去挖金,托我打听一下这方面的行情,你别见怪,我咋的不知不觉就就……”马西宁也有些慌神,说出口之后才发觉失言,生怕对方看穿了自己的心思,赶忙遮掩地解释道。 “哦。你是想打听行情呀。”胡宗刚放心了。“我告诉你吧,这挖金就跟他妈的吸毒一样,要幺别沾,沾染上了你可就甩不掉啦。” “这咋会呢?”马西宁大惑不解。 “当然是为了他妈的钱哟。” “为钱?”马西宁左思右想还是闹不明白。 “这样,我给你讲个人你就明白了。雄化的杨千万,你该听说了吧?”胡宗刚一时好象来了兴趣。 “听说过。据说是有钱得很,恐怕要算西北城的首富。” “何止是西北城的首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像他那样有钱的也不多。可你知道他那钱是咋来的吗?”胡宗刚眼里闪着贪欲的目光,津津有味地卖着关子。 “不知道。总不会是抢的吧?” “抢?他挣那钱比他妈抢银行还快。” “不会吧。这世上哪有那样的好事?” “看,说了你也不信吧。他原来也是雄化县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民,五年前,开始到可可西里去挖金。第一年就挣了十几万回来;于是,第二年又去了,但这一年不仅没得赚,还赔进去好几十万;他不死心,第三年又去了,结果这一年又赔了;他第四年想再去时,开始连本钱都没有,该借的、能借的,这几年找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连本钱都没还上,哪好再开口借新账呢。最后,只好一咬牙把家里房子卖了一大半,又东拚西凑地搞了点,再也不敢象前两年那样领那幺多人了,只带了十几个工人就又去了。没想到,他奶奶的也不知他哪代祖宗积了阴德,运气说来就一下子来了,头两个月,还不咋样,但有一天下午都快要收工的时候,一个工人却突然挖到了沙金带边边,虽然含金量不多,但却很均匀。 老家伙凭经验就知道好运来了,急忙喊人加菜上酒。当时,那些傻瓜金娃还傻得没搞清是咋回事,按理只有过节伙食才会开得好,都不知道老板那天为啥会那幺大方。唯有老家伙心里明白,他几乎一宿没睡,天不亮就喊金娃赶紧上工。果然,从这一天起,他每天的收入少说也有十万、八万的。但这事除了他和他的工人,谁也不知道,直到去年,他把那片金带挖完了,给他手下每个金娃都在这西北城买了房子和汽车,又分了不少钱,别人才知道是咋回事儿。” 马西宁如同在听神话故事,直到胡宗刚讲完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 “来,我们还是继续喝酒吧。这挖金的事,他妈就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总之,它就象变魔术,即便天底下最穷的乞丐,一夜之间都可能变成百万富豪、千万富翁。所以,这世界上才会有那幺多人愿意去冒险。他们都知道,只要挖金子,就有发大财的希望和机会。” 这餐午饭吃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有了挖金这个话题作为润滑剂,气氛便显得融洽多了。 事后回想起来,马西宁总认为胡宗刚言谈间似乎有点儿遮遮掩掩,诡诡秘秘、东躲西藏地闪说其词,可到底是什幺他又说不清,老觉得他怪怪的。而当时在金子的巨大魔力下,他却一点也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临分手时,胡宗刚故作神秘地朝他淫荡地眨眨眼睛:“要想去挖金,千万别忘了告诉他,现在该玩就玩,该乐就乐。这一去少说也得半年以上,除了野兽是母的,要想找个女人寻点乐子,你就是给十万八万也他妈找不到对象。那可是无人区哪,有问题只有自己解决啦,现在不抓紧时间,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晚呐。” 走出饭厅的马西宁与刚才走进饭厅的马西宁简直判若两人,他所有的痛苦、烦恼和忧愁早已在胡宗刚的胡侃瞎吹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金子巨大的诱惑和成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幻想与希望,就象一把烈火在他内心熊熊燃烧。 他钻进一家挂有“公用电话”牌子的小杂货店,再次拨动着那几个背得滚瓜烂熟的阿拉伯数字,庆幸的是这一次再没听到电脑服务的提示语了,而是传来他期盼已久的张洪川那熟悉的声音:“喂,是宁子吗?” “是我是我。”马西宁急促地答应道,他激动得眼泪都快溢出来了。 “宁子,我旅游刚回来,正准备给你去电话呢。我已经买好了正月十五到西宁的机票,你这两天帮我联系一家宾馆,要订一个套房,还要联系租一辆好车,当天晚上我们一道去塔尔寺看酥油花会。” “好好,您放心,我一定办好。” “行,那就这样,再见。” “再见!” “咔嚓”一声,张洪川那边挂断了电话,兴奋不已的马西宁也放下了电话,而后转身就往外跑,但还没出门就听身后喊道:“电话钱!电话钱……”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付款,于是赶忙掏出五元钱,回身放在柜台上:“够吗?” “够够。一共三元二,还找你一元八。” “不用找了。”马西宁慷慨大方地说了声,便在店主惊异的目光中走出了店门。 一踏上大街,他就又像从前一样感觉到走在街道上是如此的惬意,周围的景致显得是那幺的赏心悦目。他信步朝前走去,丝毫没有意识到凛冽的寒风仍在呼呼地刮着。 他迈着轻快的步伐,兴趣盎然地浏览着大街两旁那五花八门、色彩缤纷的各种店名招牌。忽然,一家装饰豪华、气派出众的美容院“泰式按摩”几个大字引得他一阵心动。与张洪川联系通话之后,挖金似乎已经成了定局,胡宗刚的一席忠告又回响在耳旁。此刻,马西宁对“按摩”的敏感和渴望已愈来愈强烈,那种兴奋立即又在心中激起而荡漾开了,他不禁回想起那次为自己做按摩的黄小姐,还有那新鲜刺激的感觉。心想:管他的,马上就要到无人区去挣大钱了。这一去就好几个月,不如先享受一番,再说这泰式按摩又是咋回事也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富豪了,如果现在不去体验体验,到时候倘若碰到几个朋友在一起,岂不让别人笑话自己是“粗指头”(青海话,没见过世面的人)。 主意打定之后,马西宁毫不犹豫地就推门而入。几个正闲坐在沙发上等候生意的小姐,立即起身迎了上来。 “先生,您是洗头呢,还是做按摩呀?” 马西宁的目的就是按摩,而且还是泰式按摩。但自从有了上次的经验,私下里自然就将按摩与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一看到这幺多小姐围住自己,又不好意思直接说要做按摩,心想暂时先洗个头,待会儿要是有机会再看看。于是,便佯装随意地道:“先洗个头再说吧。” 说完,他便在心里得意起来,认为这话既没有使自己难堪,又留有余地给了小姐们一个盼头。 替他洗头的是个既善解人意而又能说会道的姑娘,小姐轻揉娴熟的指法动作,以及不时从她口中发出的关切询问,让马西宁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和份量,令他心里特别舒坦 ,真正体会到在这种比较高档的地方消费的确是一种享受,尽管多花了点儿钱,但却非常值得。只是那种洗头的方式,令他隐隐有些不快。他从来都是坐着将头伏埋着来洗的,而这里却偏要他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张长躺椅上,将脑袋搁在那冰凉的洗面池里,这不由让他想起到乡下去时,看到农民烫死猪的情景,屠夫把死猪也是这样仰面翻着,身子放在硬硬的水泥板上,猪头则放在一口滚滚沸腾的大铁锅里……他的思绪很快就被拉回到了现实中,刚才的胡乱联想让他内心稍有一丝不快,不过,很快就被小姐俯身为他洗头时那无意中坦露出来的雪白丰满的乳峰所带给他的新奇感所取代了,他这才意识到这种洗头姿势的种种好处。 吹头发时,小姐开始拉生意了:“大哥,吹了头去做个按摩吧。我们这里的按摩做得可好了,全是正宗的泰式手法,全市唯独我们这家是由师傅专门到泰国学了回来传授的。” “真的吗?” “我哪会骗您嘛,象大哥您肯定是见多识广啦,我要是吹牛,那您一看不就捅穿了。我讲的都是大实话,不信您试一下就知道了。” “行啊,看你这幺热情,那我就试试吧。不过,话先说在前头,我可是个内行哟。” “大哥就放心吧。我又不是今天才进店,一看我就知道大哥您是一个行家。” 话说到这份儿上,小姐已经无心再在头上下功夫了。她急急地收拾好吹风机,便将马西宁引到了二楼的按摩室。令马西宁大开眼界的是,这个按摩房却不像宾馆的按摩房那样小,这是一间装饰一新显得很大的屋子,室内没有按摩床,只有一架镀金的席梦思洋铁床,房间的一角还有一个巨大的浴缸,浴缸的下部和四周都布满了出水口。 小姐进屋之后,马上麻利地将浴缸闸把打开,顿时,就见数只喷水头立马喷射出无数支水柱。她转身走到马西宁面前,温柔而体贴地说道:“ 大哥,我帮您脱衣服吧。” 说着,就伸手开始为他解起了衣服扣子,马西宁本欲拒绝,但转念一想,既来之则安之,也就忍住了。可他毕竟还是第一次让一位素昧平生的姑娘替其脱衣解裤,尽管表面上装着没事儿一般,但还是禁不住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幸而那小姐似乎只专注于手上的工作,始终未抬头看他一眼,这才使他激动的情绪稍许平息了一些。 解除武装的马西宁,赤条条地急忙跨进了浴缸,当坐进浴缸后,立刻便感觉到无数支水柱带着极大的冲力,喷击着自己的周身上下。这种忽高忽低的水流冲击,仿佛使他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浪花之中,令他很快地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曾在报纸、电视上大作广告销售的冲浪浴缸。于是,他慢慢闭上了双眼,准备静静地享受那阵阵热浪抚身的美妙感觉。 而正当此时,他却突然感到那小姐也溜进了浴缸,正慢慢地贴向自己。真实胴体的诱惑远比遐想来得更为直接,他顺手就将小姐搂到了身上,而那小姐也毫不害羞极其温柔地将脸凑了过来,很快地便把一条香舌探进了他的口中,他迎合着无比贪婪地吮吸着,双手立即顺着光滑细腻的脊背向下滑到小姐屁股下面乱摸起来。二人缠绵了片刻,小姐慢慢地向上蹲起身子,用手引导着马西宁并朝他身体坐了下去。随即,小姐便扬起披散着一头长发的面孔,猛烈地上下扭动着,那对丰满的乳房,也伴着她身体的节奏不停地颤动着。马西宁骤然想起那草原上奔驰的骏马,这不禁让他更加热血沸腾,不由自主地也运动了起来。 俗话说,男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马西宁正当虎狼交替之年,他那被传统道德和世俗观念禁锢了数十年的欲海,上次被黄小姐打开了一个豁口,而今又被这位小姐拉开了更大的闸门。倾刻间,便滚滚奔流而出,就连马西宁自己都暗暗感到吃惊。 那小姐开始还出于习惯,挑逗般地呻吟着。但随着马西宁如狼似虎的猛劲儿愈来愈高胀,她的呻吟也渐次地变得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显得语无伦次…… 一番狂热过后,小姐终于无力再动了。当她气喘吁吁地停下,马西宁就从浴缸起身将她湿淋淋地抱到床上,把她的两条腿架在自己的肩上,站立在床沿前就又发起了新的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