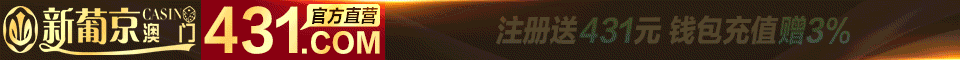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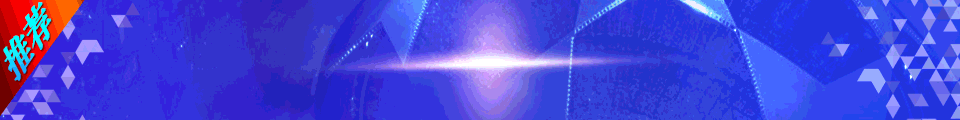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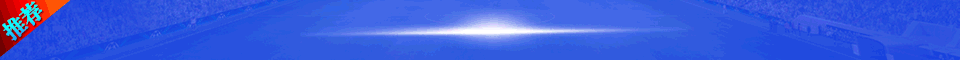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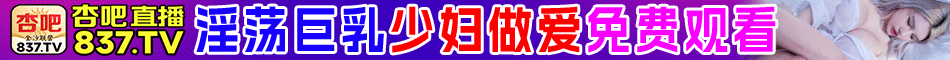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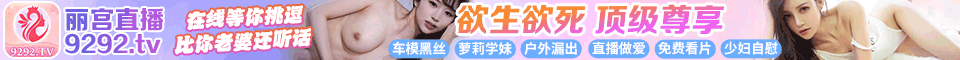
被侄子给肏了
我跟侄子发生关系了。
侄子比我小26岁。
莫非我有潜在的儿子情结?可我跟儿子挺疏远,儿子跟我也不亲。
难道正因为这个所以我格外喜欢年轻小伙子?
我亏欠我儿子太多?
也许我用我侄子补偿我儿子?还债?
我侄子22岁,是我亲侄子。
我们两家儿离得远,来往不多,逢年过节串串,送个点心匣子,喝杯茶,也就这样。
每年我哥给我送一袋米,觉得我一个女人过日子不易,买大米吃力,我感谢他。
其实我离婚17年下来,大白菜,换灯泡,什么事儿都自己扛。
今年元旦,他们全家忽然来我这儿,带了好多苹果、橙子,还有六条平鱼,得五十多一斤,我从来都舍不得买,顶多在超市水产柜台,弯着腰近距离一眼一眼观察。
现在我一眼一眼打量我侄子,我真不敢相信几年前那个小毛 孩子现在成大人了。
他长大了,变高了,大宽肩膀,模样挺俊。
我哥嫂跟我说,我侄子寒假上英语强化班,离我这儿近,腿着五分钟,离他们家太远,说在我这儿住成不成?
我说住呗,你们都来住才好呢。
他们走了,留下一兜子苹果、一兜橙子、六条平鱼,还一半大小子。
平鱼散发着腥气,鱼腥填满每一立方厘米。
现在孩子长得真好。
我在他这岁数要啥没啥。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可能吃的里头残留农药激素甲基汞啥忒多,催得这么结实这么老高。
十七年,我一人。
家里只有一张床,双人的,是离婚以后买的。
旧床折旧卖了,太多伤心故事。
当初买这双人床的时候还怕人说闲话,后来想开了,我该在乎谁?我这儿一年到头撑死了来几拨串门的?万一我要是找着合适的呢?带回来挤一小窄床?苦谁不能苦自己,穷谁不能穷教育。
还没黑,他就问:「姑,我睡哪儿?」我说睡床呗睡哪儿,你就跟我睡。
他瞅瞅我瞅瞅床,眼神怪怪的。
我也打起鼓。
他在我眼里永远是孩子,可现在他已经比我高出一头。
他是大男人么?不,还得算孩子。
我眼前站的这人到底是什么?装傻充愣的白面书生?还是一头性成熟的小牲口?
我一普通人,就住这么一套独单,44平。
14 岁,我有过旖旎梦想,我知道我长得不错,梦想中当然就更加柔美婀娜妩媚多情,是男的见着我都走不动道儿。
24岁,我有过远大目标,那会儿年轻。
谁没年轻过?34岁,我还不服呢,不信邪,正较劲。
到44岁,认命了。
其实我一直特清楚,我知道我的命运不该这样,可偏偏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男人被小妖精勾走了,儿子也不跟我,存摺里那点儿盒儿钱一般不动,每天上班累得要死,长相也靠不住,不敢照镜子了。
离了以后找过几个,都不中意。
心灰意冷。
我这辈子就这么着啦。
现在大侄子进了门儿,我也就是灵光一闪,马上就笑话我自己:都徐娘了还自作多情,再说了,这是带血缘的,砸断骨头连着筋。
瞎打啥鼓?碎觉碎觉。
彻底黑了,也熬困了。
第二天我得上班他得上学。
我叫他先去洗,他叫我先洗。
洗就洗。
我脱掉毛衣,进了卫生间,脱了套头衫搭钩子上,回头瞅瞅门。
一人十七年,十七年安静过活,洗澡撒尿没关过门,没必要嘛,给谁关外头?可现在不一样,一男的就在我浴室门口儿转磨,像憋了八斤屎。
我当姑姑的,洗澡不关门,不合适;关吧,又疏远了。
我这是防谁呢?摆明防他。
他那么可怕么?
本来没事儿,我这儿喀啦一拉门儿,等于暗示他:这儿一女的啊,记住喽,你是男的。
本来无一物,强化惹尘埃。
等裤衩儿脱了,浑身光溜溜,我实在没勇气再敞着浴室门了。
我尽量不出声儿地拉上一半儿门。
拧开花洒,温水喷淋。
今儿我奶头儿怎这老敏感这老硬?外头,我大侄子已经比我前夫还高还壮了。
我倒是一直喜欢高大威猛型儿的男的,大宽肩膀,大硬胸肌,下边也大大的硬硬的顸顸的,能给我顶得魂飞魄散内种。
我哥嫂明知道我这儿就一张床,还把我侄子送过来,是真天真?还是考验我?还是心照不宣给我送个杀痒大礼包?
越想奶头儿越硬,越想下边越酸,恨不能手指头伸进去通一通。
忍啊忍,我还是忍住了。
浴室门毕竟没拉严。
我一大半的心思都盯着门口、悬在门外。
我早想好了,只要他进来,说要撒尿,我就,我就,我就一把薅住他,让他尿我里头。
这想法儿让我脸蛋儿焦红。
我居然这么淫荡对我大侄子想入非非?
就这样,心扑通扑通,他一直没进来,我澡也没冲好。
八成儿他比我难熬。
我的动物性本能占据上风,命令我的手指来到屄豆上轻轻按摩。
快感呈几何爆炸递增。
屄豆已经肿胀,饱满充血,赛开心果。
我这豆还从来没胀到过这个程度。
我真是骚得可以?揉搓不到二十下,我已经听不见水流声。
再揉两下我就能完蛋。
我的身体我熟悉。
这么些年来,每月总有固定减压时刻。
我想要的节奏、我喜欢的频率、我偏好的部位、时间火候,没人比我烂熟。
可偏偏就这两下,我没下手。
我给谁留着?给他?当时来不及深究,关水、擦乾,裹浴袍出来,脸蛋粉红,气喘吁吁。
电视哗哗开着,客厅没人。
我裹着浴袍光着脚走进卧室,还是空的。
走进厨房,也是空的。
邪门儿啦。
啥情况?忽然窗帘一动,一人闪出,满脸通红,是我侄子。
我想起,阳台通浴室窗。
我刚才冲澡他都看见了。
我正想发作,他噌一下蹿过来给我抱住,他胳膊钳着我所有的肉,强悍有力。
我还没挣开,他的嘴已经亲上我的嘴,我喊出的话全被他嘬进肺。
我闻他身上好像总是飘出平鱼的腥气,挺硬内种腥,贼腥。
我对气味天生敏感,加上这些年一人过惯了,过独了,刁了,不能容人了。
我使劲儿推他,他不松口儿。
我玩儿命跺他脚,他不放我。
我再推他,忽然感觉屄屄被他一把兜住,我浑身的力气一下都被泄掉了。
他的手指不停地摩擦我的下体,当时我就懵了。
我心理防线本来就弱,他这么一弄,我归零,心理防线全线垮塌,全投降,全敞开,然后就是很久没享受过的快感。
我很冲动。
我出格了。
我知道每个游戏都有规则,我违背了游戏规则,可我此刻特舒服,太舒服,我不想停。
我大侄子在奸我,可我没力气反击他。
是真的没力气。
洗完澡本来就浑身轻飘飘,动情大穴又被钳住,加上本来就在幻想被侵犯,所以过场走完,身子立刻软掉,比棉花都软,搂着他的粗脖子,半睁着眼,期待地等着下一步进犯。
这时他眼神沉着镇定,下边的手法异常精准,招招击中女人的中心。
这让我震惊:我碰到老手啦?
看看他,这么稚嫩,怎么会是老手?上唇胡须软软的,尖端变细,淡棕色,应该还没剃过;说话bia-bia 的,嗓子正倒仓,他能弄过多少姑娘?可他现在偏偏弄得我要死不活。
我浑身发烫,尤其后脑发热。
我把一切礼教所有教条啦弟子规啦多少孝多少贞啦统统Shift+Delete…我专心享受他的舌头他的手指。
男人的舌头男人的手指。
十秒不到,我就发现我已经疯了似的往上挺着腰,哭着高了。
我没哭我的命,没哭我的苦。
纯粹就一生理反应。
太强了,受不了,不适应。
来太晚了。
早点儿多好?还有就是,怎偏偏是他!我们以后咋整?
刚从被他指奸的虚脱里清醒过来点儿,冷不丁觉得屄门被扒开,一条大的、热的、粗的、硬硬的东西顶进来了。
硬硬的东西插进了我的身体,我都这岁数了,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我赶紧闭上眼睛,学鸵鸟。
我不敢睁开。
黑暗里,我知道我的脸被捧住,那双手强有力,呼吸带鱼腥。
我知道我被肏得快死,奶子狂飞,跟白痴似的。
我知道我的宫颈口被那条滚烫的东西冲撞着,快感越来越密集地冲撞我的丘脑。
我知道我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享受过这种快活了。
我咬着牙,不松开,正像不敢松开我的眼皮。
这一刻,我要深深沉浸在动物界的快活里头,加入野生动物的节日。
耳边是咆哮的喘息,是白热化拉风箱,振聋发聩,烈焰蒸腾。
这完全是成年男的喘息,粗野混帐,兽性十足。
我屄里夹着一条硬鸡,野蛮活塞,力拔山河,拖浆带水,泛着泡沫。
这鸡巴年纪轻轻,跟我还沾亲带故,我不该放他进来,我不该继续。
我心说,这是乱伦,乱搞,乱来,乱套,我也想提醒他,可我张不开嘴。
我又闻见他身上的平鱼的腥味儿,闻时间长了适应了,觉得也挺好闻的。
好比常年浸淫墨汁,久闻不觉其臭,反觉「书香」。
你要是养过马,时间长了会喜欢上马,包括身上的马味儿,马的肌肉,马的耸动,马的声音,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你的生命跟马融为一体。
烈马大展宏图,在我身上撒欢儿。
我应该推开他,立刻推开他,无条件推开他,可我浑身软绵绵,都快化了;胳膊倒有把劲儿,却搂着烈马脖子,死死钳住。
我舍不得清醒、舍不得让他停。
他完全是报复性地在我肉里发泄,顶撞,征服,弄得我生疼,感觉他对女人有仇,不共戴天。
忽然我的两条胳膊被他举过头顶,我的胳肢窝被热热的狗嘴亲着。
钻心的痒让我浑身扭动,像蛇一样。
即使这样,我还是舍不得睁开眼睛。
所有的罪孽都来吧,来吃我吧,吃吧,孩子,管够。
狗嘴唇狗舌头对我痒痒大穴的舔弄贪婪凶残令人发指,狗鸡巴对我下头的顶撞蛮横无理穷凶极恶,这混合型刺激超过了我承受极限。
在狂笑中痉挛,在痉挛中高潮,高潮中下头一热。
括约肌背叛了我。
我尿了,还没少尿。
也可能是sis朋友们老说的「喷」了。
当时已经停不下来,身体完全不由我控制,各肌肉群组强有力收缩,阴道的痉挛和尿都停不了。
尿尿呗。
放纵自己。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两胳膊上举被侄子按枕头上、胳肢窝被侄子亲着舔着,下头被侄子肏得哗哗喷尿、湿透被缛。
潮头过去,我浑身没劲儿,劲儿全被烈马卸掉。
多年前跟前夫苦苦博弈,最后完败,我以为我的心早死了,热情已被耗尽。
没想到我又活过来了。
我从心里感谢我侄子,这个年轻男人,他给了我新生。
我涌起一股激情,想为他做任何事儿,满足他、留住他,让他开心,让他永远属于我。
他干一会儿就拔出去,给我换一姿势,继续调情调戏,等我实在受不了,他才进来,狠狠给我杀痒。
他掌控全局,从容自信,动作到位,沉稳老辣,节奏跌宕,大开大阖,放得开,收得拢,张驰有度,行云流水。
他像贝多芬,像上帝。
他的岁数完全不匹配他的老练,这种老练完全是多年浸泡流水线的熟练工人。
现在的小年轻儿都这么早熟?还是叫我赶上一特例?
一直到听见也不谁肚子叫,才意识到都饿了。
一瞅,已经后半夜。
我下床洗手,去弄吃的,精力充沛,走路噔噔的,眼睛发亮,不困,一边儿做还一边儿唱呢——说天亲,天可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
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 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
说爹妈亲,爹妈可不算亲,爹妈不能永生存。
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一捧黄土雨泪纷纷。
说儿子亲,儿子不算亲,人留后代草留根。
八抬大轿把媳妇娶,儿子送给老丈人。
说亲戚亲,亲戚可不算亲,你有我富才算亲。
有朝一日这日子过穷了,富者不登穷家的门。
说朋友亲,朋友可不算亲,朋友本是陌路人。
人心不足蛇吞象,朋友翻脸就是仇人。
说闺蜜亲,闺蜜可不算亲,处心积虑套你隐私。
一旦触及她的利益,闺蜜翻脸就不认人。
说丈夫亲,丈夫可不算亲,背着你在外边找情人。
沾花惹草种下孽,死心塌地闹离婚。
说同行亲,同行可不算亲,勾心斗角好寒心 名夺利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
要说亲,大侄子最亲,侄子跟我心连着心。
轻拢慢捻抹复挑,跟我是砸断骨头连着筋。
夜宵做好了,汤汤水水,热气腾腾,跟他一起吃。
饿得透,吃得香,越吃越想吃。
一边吃一边瞅他,觉得他是这么精神,这么好。
我像花痴一样看他,像白痴一样说着大胆的话。
那些话我从来没说过,跟我前夫都没说过。
我整个儿换了一人。
他偶尔抬头,说我脸色儿好。
我得意半天,说都是他给我滋润的。
我怕他累着,我已经开始盘算明天下班路上去买一只三黄鸡回来给他好好补补。
吃完想起他还没射,上床再战,添酒回灯重开宴。
他提出要插我嘴,我忙不迭答应,然后张开嘴瞅着他。
我从来没让人插过嘴,前夫没这要求,我也不知道还能这么玩儿。
侄子过来了,近了,更近了,他那大东西直挺挺,大炮口儿挂着长长亮丝儿,炮口对着我眼睛,感觉好像要戳我眼眶子里。
我一点儿不怕,眼皮都没眨。
如果他真想戳我眼眶子,我就让他戳。
人有时候吧,真能涌起雄壮的英雄主义。
他身上那股腥味儿,怎么就让我迷醉?可能气味儿能给我催眠。
人陷进某种特定情境里头,就能鬼打墙,你就出不来,被障住,被魇住,多巴胺内啡肽或者别的胺别的肽还有大脑神经元、递质和受体、神经通路所有因素共同作用,你就能干出疯狂的事儿,比如逼急了打急了顶到那儿了,就真能自己走向铡刀、枪眼、火刑柱。
大炮捅进来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要吐,刚吃的那些全在嗓子眼儿那儿翻腾,争先恐后要喷出来。
提醒sis 的朋友们,插嘴这活儿,真不适合饭后。
说白了嘴就不是让插的家伙,嘴就是吃饭的家伙,亲嘴用还成,那老长那老顸一棍子戳你嘴里你自己试试啥感觉。
当时他身上的气味儿他蛋蛋的气味儿他大炮的气味儿,有腹股沟捂出来的汗味儿,汗可以是又臭又香的,有雄性激素睾丸酮,有蛋白质的清香,有肉香,还有一点儿味精那种鲜香,合在一起,浓浓的,腥腥的,香香的,臭臭的,单宁丰富,馥郁芬芳,复杂混合,致幻催眠,让我魂不守舍,甚至帮我克服了呕吐反射机制。
我仰着脖子张大嘴巴,满眼是泪,望着国王,战神,我的魔鬼,让这魔鬼可劲儿往最深处弄。
其实呕吐反射是没法抗拒的。
等我回过神儿来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吐了N多车了,从下巴脖子到胸口肚子全是刚才吃进去的汤汤水水,奇怪的是我居然没觉得难受,也没觉得呕吐物难闻,可见催眠效果之狠。
我还在坚持叼他,而事实上我已经吐得稀里哗啦了。
呕吐物的气味儿好像也有催眠效果,跟「平儿鱼的腥味儿」混合之后,形成更好闻更富含营养的浓香。
魔鬼得寸进尺,插得越来越深,还按住我后脑勺,玩儿了命往我嗓子眼儿紧里头戳。
瞅他那架式他是打算一路顶进我胃小弯。
英雄主义能激发人类潜能、能创造世间奇蹟,真的,不蒙你。
在英雄主义顶撞下,我含下了他那大炮筒的四分之三,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极限了。
他呼嗤带喘,搞得好像马上要给我啥恩赐,只是他的俩手攥我头发弄得我疼。
我居然也忍了,连连点头哈哈地吞他那东西。
胃里酸水儿就没断。
酸性口液从我下嘴唇流我下巴上,又从我下巴往下拉着长长的丝儿往下垂往下飘,一直到我小肚子上。
垂到我小肚子上的我自己的口液已经冰凉,不那么忒舒服,不过我的注意力全在钢炮上、在他的满足上。
我想的只有一件事儿:满足他。
听他的声儿,我猜他马上就要射了。
我要让他快活、让他得到最大的快乐。
我张大嘴,试着最大限度地敞开喉咙,让他的大鸡往里、往里。
鸡头已经侵犯到我从没被人侵犯过的深度,大夫的压舌片都没探过我这么深。
我一边儿被他搞喉咙一边失控地呕儿啊呕儿啊喀喀喀喀地往上乾呕。
当时我豁出去了,已经掫出来了,没货了,反正已经这样儿了,就这么下去得了。
我不停,我要让他不受打扰不被中断地享受极乐快活,也许他喜欢的恰恰是射在女人喷涌呕吐物的热热的嗓子眼儿里头?
我这辈子只喝过两次酒。
第一次是十九岁,夏天,跟一男生去一小酒馆,喝完难受死了,据说后来是被那男同学扛回我家的。
第二回是结婚,喝了几小口,高兴嘛,以为这辈子踏实了、有指望了。
结果呢?嘿!现在我想喝,不管是酒还是精。
我还从没喝过精呢。
啥口感?
他会觉得射我嘴里特豪迈吧?把姑姑征服,瞅着姑姑咽他精华,特变态吧?
我够淫荡吧?我是荡妇么?
大脑前额皮层一阵明显发热,脑袋瓜儿一片空白,失忆,失禁,失控,失掉所有的控。
我猜等我撒手人寰那个瞬间,差不多也这感觉,特温馨,特舒服,放松,放纵,松弛,撒手,轻飘飘,像泡温泉,像醉酒,云中漫步,吸了粉儿,飙车,狂怒,面对行刑的枪口,啥都无所谓了,肏你妈啥罪恶呀伦理呀下辈子吧,啊。
他忽然加快了整我嘴巴的节奏,呼哧带喘当中断断续续说:「姑,我要射你嘴里!」当时他已经快给我小舌头顶烂了,我含着他鸡巴、一劲儿点头。
我是真心希望他直接射我嘴里、射我嗓子眼儿里、射我胃小弯里。
我今生从没允许任何男的射我嘴里。
可我当时就那么想、那么渴望、渴望新的尝试、新的刺激、新的玩儿法,渴望更放荡、更淫荡。
可能是一种接近献身的轰轰烈烈的雄壮的什么精神在激励我,可能我被卓娅奶奶要么胡兰奶奶附了体了?反正我忽然特别特别冲动,心跳贼快,脑仁儿嗡嗡的,眼睛瞅啥都视野模糊内种。
他彻底加快了肏我嘴巴的频率,吭嗤吭嗤得越发不像人了,整个一疯子。
我在心里默念着:搞死我吧、搞死我吧。
我要牺牲、要sacrifice.这很神圣的,你知道么,为一信念、为一念头儿,后脑一热,啪叽就捅出顶天立地一事儿,瞬间挺伟大的,金陵十三钗那句 w ǒ-men dòu-k ì(我们都去)10620 ,那是英雄主义,以卵击石,纯傻屄。
他到最后没捅进我胃小弯,也没射我舌头上。
是我对他构不成足够刺激?他有别的打算?还是他嫌我已婚、而他没有婚史?我问了,他没说。
他再次撤出去,还硬梆梆,然后舔我肛门。
这又是我第一次体验,神奇怪异,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立起来了。
快感太强,没法忍受,男人还能对女人这么样?我前夫从来没舔过。
现在我侄子是纯为讨好我还是他真喜欢这样?他舌头在我肛门口游动,时软时硬,还往里头钻,钻得我整条消化道舒服到嗓子眼儿。
忽然感觉有东西进我阴道里了,是他手指头,在里头狠命鼓捣,像挖宝。
倒挺好受的,不同的快乐奇特混合,绞在一起,把我弄死。
我缩着脚趾缩着腰,又高潮了一回。
从坡顶下来,全散架了,脑子一片空白,满身大汗,撅屁股趴那儿,动不了窝儿。
敢情有这么多种玩儿法。
我之前几十年真是白活。
他的东西进来了,这次进的是不该进的地儿。
我腰被他攥着,排泄的地方被插着。
鼻子里填满平鱼那种腥味儿,浓烈刺鼻。
我撅着屁股,在做畜牲不如的事儿,可我这会儿正美,正酣。
我莺声燕语,一半是迎合他,一半是自发。
弄后边居然也能舒服,也能高。
我高了,不知道是他从后头隔着一层肉顶到我前边还是我后边的神经末梢也同样敏感。
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我美了,这是最主要的。
战神又战略后撤了,东西还硬着,到我脸上,散着香气,香香的,臭臭的,好比咸亨炸臭乾儿,又臭又香,韵味十足,回味无穷。
有人觉得香菇香,有人一口不吃。
有人喜欢榴莲,有人爱吃臭豆腐。
臭豆腐诱人之处正在于它香香的又臭臭的。
我那年去绍兴,刚一进咸亨酒店,就被浓郁的臭香味儿包裹,整个店包了一团云雾,我在云雾里走,跟梦似的,跟现在似的。
炸臭乾儿上来以后,第一口不适应,后来越嚼越有滋味,回味深厚,让人上瘾。
餐后出了店,觉得没过瘾,就找路边小摊,切小块扎细竹签上那种,瓦灰色儿,炸至灰黑,街灯下就白嘴儿吃,什么酱汁都不蘸,吃了一串又一串,诱人的臭香在身边弥漫,进到我身体里,就像现在。
现在,战神跪我脸边儿上,凶器指着我,分明跟交警似的。
我张开嘴,把长长的粗粗的臭乾儿迎进来,暖他,润他,舔乾净他,崇拜他。
他让我无数次高潮无数次美,他给了我一辈子都没体验过的快活。
凶器在我嘴里一直硬着,不撤。
不撤我就一直舔,让他捅,表示驯顺。
他这么老到,我忽然闪过一念头:他是魔鬼。
对自己太自律自控其实挺可怕的,跟机器似的。
算了一下,他已经弄了我十多个小时了,这超出我前夫干过我的长度总和。
我前夫每次顶多半分钟。
我问他难受不难受,他说还行。
你说他真是人吗?
我舔着刚弄过我后边的凶器,不觉得下贱下作,不觉得恶心,反而满心欢喜。
舔着舔着冷不丁清醒过来,自己吓一跳,吓一身汗。
现在这真是我么?我这是干吗呢?这不作践自己么?我是他姑姑,端庄得体,一向稳重,我这是毁我自己呢,天亮我怎见他?以后我怎面对我哥?不容我多想,下一个大浪劈头盖脸又砸下来,把我淹没,把我拖回无底深渊。
大粗硬家伙又闯进我下体。
我快活地坠落,重力加速度堕落,叫唤出更下贱的声音,干出更多不可思议的事儿来。
他带着我拉着我舔着我顶着我到了一仙境,这儿可能是性游戏能达到的至高境界。
不知道他什么感觉,反正我从来没上过这么高的地方。
说实话我前夫跟我做爱不多,他老说累老说累。
我是传统女人,哪儿好意思一二再再而三提要求?
累就养着呗,不做就不做。
我哪儿能跟荡妇似的没完没了求他。
可现在我迷糊了:莫非我还就一荡妇?闷骚了二十几年,强忍,欺骗所有人,欺骗我自己。
其实荡妇有啥不好?为自己活,为自己爽,真诚,不装屄,长寿,不遭雷劈。
我维护这个维护那个,到最后我的家呢?碎了,成了碎片儿,团不到一块儿;老公、儿子全跟我不一条心。
这么多年我正经得到啥了?就一小独单。
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可怜我,给我派一童男子儿来帮我、度我。
我要再不珍惜这机会,谁还老帮你?
我抓着他,死死箍着他,可是不敢看他。
他喷白烟冒热汽,混横不羁,气势汹汹,这是一头肏屄兽,把我变成淫水母。
我真的乾渴到极点了。
我好像在报复前夫,报复此前受过的所有的委屈不公,玩儿命补偿我自己。
他捅会儿舔会儿,冲我说着可怕的话。
我听着顺着答应着,闭上眼睛设想那些流氓事儿真发生。
他那家伙里头可能有骨头,要不然的话怎能一直不软?他的运动没有尽头没有终结,他热爱这运动。
他要不是我侄子该多好?无数次中场休息,喝水、撒尿、聊天。
我问他:「你嫌不嫌我老?」他说:「你不老啊。
我还就爱肏四十来岁的娘们。
」「为什么啊?」「骚哇。
四十多岁的那是真骚,放得开,真败火。
」「告诉我实话,你糟蹋过多少阿姨?」「没多少,也就三十来个吧。
什么叫糟蹋呀?我这叫助人为乐,替天行道。
」说完又扑上来跟我绝斗。
我俩像末世仇家,又像棋逢对手,网球名将,玩儿命对抽,一千回合,谁都不累,大汗淋漓,还乐在其中。
我这辈子没出过那么多汗。
真出透了,床单是湿的,枕巾湿了,褥子也湿了,哪儿哪儿全都是湿的。
有时候我能听见床腿儿床脚嘠吱嘎吱,楼下邻居准能听见。
听见就听见。
我为谁活?
为这个为那个都活大半辈子了,我都快绝经了我。
闭上眼睛勒死战神,嘠吱嘎吱又听不见了。
你在极乐瞬间,耳道是封闭的,眼睛也一样,跟许仙最后在金山寺似的,或者更高境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想都不想,顺其自然,归隐山林纵情嚎叫,心甘情愿沦落为兽。
忽然想哭。
这些年我过得太苦了。
我太委屈我自己了。
什么什么都我一个人,我太难了。
我深感自己渺小、无助,深感绝望、孤独。
偶尔想了,自己弄弄,完事儿以后更难过。
我不是开放型的女人,特别想的时候也有,一般就是每月倒霉之前那几天,生理的需要靠自慰解决。
弄,谁都会,杀痒的法儿谁都有,问题是,孤独是绝症,它这没治。
现在,为对抗孤独,我抱紧他,也让他抱;亲他,也让他亲,让他进,让他顶,让他使劲填充我,填满我,塞严空虚,好像这样儿我就不孤独了。
窗外泛起淡蓝色天光。
床上,一朵大花在哭着怒放,补偿迟到的享乐,补偿一切。
人太缺什么就会找机会恶补。
恶补总会过梭,会犯错误,矫枉过正,失去灵魂,找错对象,自取其辱。
我脑子里头乱了套,开了锅。
事儿出了,事儿是错的,我是长辈,我必须断。
可这东西能断得了么?以后我怎面对我哥?他会不会怀疑?会不会闻出蛛丝马迹?发生关系是大事,身体、想法、内分泌都剧变,地覆天翻。
我相信,发生过关系的人,身上会发出新的味儿,跟以前体香不一样,自己能闻出来。
别人,靠近的话也能闻出来。
我怎么遮掩?他回去住以后会不会说漏嘴?
我问他说不说梦话?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不说,还说他们知道就知道了,都是家里人,怕啥。
他这什么逻辑?这事儿寒碜,可千万不能说出去,跟谁也不能说。
在有的地方,我们这种得浸猪笼,或者被人用大石头砸死。
他还是满不在乎。
吃过早饭,他跟我说想接着干、不想上课。
我说不去就不去,但是不能再弄了,必须睡觉。
身子要紧,这么干谁受得了?他趴我身上鼓捣了一会儿,趴下头不动了。
我一瞅,着了。
我也困,可我得上班。
上着班,想着家里趴一美少年,我心里忽悠忽悠的。
我脚步发飘,嗓音都比从前好听了。
中间上厕所的时候,擦出好多好多黏液。
想起昨天夜里,我下头又痒痒了。
毒瘾发作,凶猛暴烈,你根本招架不住,你扛不过去,你只能顺着他。
手指滑进来,动着,脑袋里头一片温热,人事儿啥都不想,只惦记满足兽性。
解完了骚,提好裤子,对着镜子照,镜子里那女人满脸通红,嘴唇潮湿,妩媚招人,骚货一枚,闻着自己手指。
我已经馋成这样儿啦?我是罪人。
我后悔了,我不该由着他。
我必须弥补,可我洗得乾净么?我再也回不到我原来的形象,他也不。
我该怎办?从此将错就错、当他秘密情人?
或者跟我哥说、说我对他好、他也对我好、让我哥成全我们?对,我嫁给他就完了。
我们到别的地方,苏州吴江,嗯,我喜欢那地方,乾乾净净,人少,路宽,没人认识我们。
我彻底疯了。
一女人,都这岁数了,被搞了一宿,居然就能痴呆到这程度。
我要真说了,我哥非给我送疯人院去。
不行不行,不去疯人院,吴江也去不了,还是得断。
下班买了三黄鸡,买了菜,两大兜子,沉死我了。
回来进楼道拐角猛抬头撞见一邻居,认识,打招呼。
我一惊,浑身一激灵,三黄鸡好悬没掉地上,嘴也不利索,答非所问,慌慌张张,脸色都变了,赶紧低头上楼。
进了家,手麻,沉的,吓的。
他真没上课去,我进门的时候他刚起床。
我定定神儿,觉得邻居瞅不出来,应该也没闻出来。
洗洗手,煲上鸡,洗菜。
他过来蹭我,摸我,我板着脸装没事儿人,闷头做饭。
他手伸进我衣服,贴着肉弄我。
我说,「姑姑错了。
咱别这样儿。
」他跟没听见似的,嘴唇身子手脚全贴上来,十足的章鱼,你根本做不了饭。
奶头被他捻硬,下头被他鼓捣出水了,心长草了,装不下去了。
放下菜,转身拉他上了床。
那天的三黄鸡差点儿糊了锅。
我看他是那么好看,看着他我心里是这么激动,激动得快晕过去了。
我眯着眼,微笑着,什么都不用说,就很幸福,心里美。
我想要他,现在就要。
我居然成了痴女一枚。
性瘾不是病,发作真要命。
人狂怒的瞬间,智商是一;动情时刻,智商是零。
我彻底被魇住了,鬼上了身,我被附了体,心甘情愿沉沦变态,失掉理智判断,醒不过来,走不出来。
其实也不是肏屄带魔力,主要是高潮那几秒钟让人分泌特别的东西,比如多巴胺大爆发,大脑释放大量内啡肽,作用像吗啡,致幻剂。
我觉得,高潮就是毒品。
————
第二天他上课去了,临走在我身上腻不够,非逼我答应他晚上接着弄,不答应不走。
我心里热乎乎,幸福。
我喜欢被人需要、被人迷恋,喜欢有人跟我耍赖。
母性被激发出来,往外流,比奶浓。
我被自己感动了。
这毒狠毒就狠毒在,你粘上他之后,你能自己给自己催眠,你给自己找藉口找理由,你压根儿不觉得他有毒,你还帮他复制病毒。
我下班回家,做好饭,听见敲门了,他回来了。
我乐着蹦着颠着去开门,笑容呱叽僵住——他和一姑娘,拉着手进的屋,跟我说,「这是我们班的。
」我从头凉到脚。
女人做事情经常是糊涂的,反正我是这样儿,情商是变数,该高的时候偏偏低,发起烧倒是高高的。
高烧中,我被玩儿得晕晕的,以为他对我真有感情了,没想到他跟我压根儿就是去火,就纯发泄。
我忽然觉得他挺邪恶的,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坏?
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们俩,还陪着笑,故作轻松,偶尔出戏,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侄子是一恶魔,吃完就搂着那姑娘进了我的卧室,不关门,直接开练。
我百抓挠心,脸上发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们那淫声秽语像针往我心上扎,不听不行啊,这独单拢共就这么大,我往哪儿躲呀我?
我走进厨房,两米乘两米,狭窄的空间压迫着我,所有的东西,橱柜、刀具、菜板、水池、灶台、锅碗瓢盆筷子勺统统朝我压过来,想要压死我。
他们在干吗?
在我床上,在我刚享受到快乐的地方,在我的地盘折腾,他们用的什么姿势?
那女孩能比我强么?我没瞅出她哪儿比我好呀。
我侄子精神头儿够棒的,他就不累么?自打他来我这儿,他就一直在战斗,他简直超人呀。
冷不丁地,那姑娘蹿出来,尖叫着,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他追出来,把那姑娘按我地砖上。
俩人跟疯子似的折腾,一点儿羞耻感没有,整个原始人。
当然了,我还不如他们,我算什么?背德姑姑,禽兽不如。
我跟全世界宣了战,我干的事儿被全世界唾骂。
所有人都比我强、比我正常。
我终于清醒了,又好像更糊涂了,浑身皱巴,难受哇,心里头特别的难过,伤感,后悔,还不能自拔,思维跟瞎线团似的,把我绕里头,缠死,走不出来。
补习班儿刚认识一天,带我这儿就弄,也不怕得病?我关上厨房门,捂上耳朵,浑身哆嗦。
我这是怎么了?事情怎么会这样?生活本来好好的,平静如水,没灾没祸也就算是福了。
好端端的,我侄子闯进来,弄了我,我跟傻瓜似的动了情。
结果现在自作自受。
我应该把他撵出去,现在就去!
我昂首挺胸出了厨房,内俩已经回了我卧室,叽叽嘎嘎,嗨哟嗨哟。
我义正词严走进卧室,面对我侄子,问:「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侄子说:「过来抬她脚,给我抬高。
」我站床边儿助纣为虐,提起那姑娘脚腕子,用力往上抬,瞅着我侄子大粗家伙往人家眼儿里捅,近距离听着噗叽噗叽声。
那姑娘四仰八叉,任我侄子肆虐。
没想到近距离听这噗叽声催情作用这么大。
我下头酸痒难熬到了极限,我使劲夹着大腿,扭着腰腰。
我侄子发疯似的干着,忽然撤出鸡巴,指着那姑娘屄豆命令我说:「过来舔这儿。
」我中了邪似的爬过去,张嘴就亲,伸舌头就舔。
那姑娘酸酸的,有点儿咸,有点儿骺,有点儿腥,跟平鱼的腥还不一样。
我这辈子打死我都没想过舔女的,可我现在真的正在舔,十足卖力,而且沉醉其中,从女女舔盘子里头还品出了甜头品出醇香。
为什么非要把寻欢对象设成异性?
我一边舔盘子,我侄子一边在我后头舔我。
床上,我们像三条狗,转圈儿舔。
我一会儿是男的,一会儿是女的。
下头湿得不像话,空虚得紧,只盼谁来捅捅。
过了一会儿,恶魔让那姑娘趴我脸上,跟我69,他肏那姑娘,让我舔他蛋蛋。
他肏一会儿,拔出来让我舔一会儿。
我刚给他舔乾净,他又肏进去。
他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完全被致幻了的。
灵魂丢了,只剩一付皮囊。
行尸走肉。
逆来顺受。
痴呆女奴。
脑瘫女仆。
一使唤丫头。
我身体上离不开他,我求他弄我。
感情上更离不开他。
我满脑子想法,疯狂大胆,每一条都不敢说出来,我知道世道不容我。
在我眼前不到五厘米,恶魔的大粗鸡巴狠狠肏着刚认识的嫩货。
那货被肏美了,骚水儿狂滋,滋我一脸。
恶魔把她两条胳膊背后头绑起来,绑得紧,都勒紫了。
恶魔薅她头发接着肏她。
她惨叫着,哭喊着,不过在我听来她正享受。
我舔她屁眼儿、掐她骚豆。
我百般的曲意逢迎,可恶魔就是不干我。
送走那姑娘,我跟我侄子说:「她挺好的。
姑瞅你们交往姑特开心。
」他不搭理我,一边唱着「说天亲、天可不算亲」,一边进卫生间打开水冲澡。
我跟进卫生间,给他搓背,帮他洗乾净。
他的鸡巴一直立着,不倒。
洗完出来我说你刚才没射呀?你怎么打算?他趴床上不动了。
我下头难受死了。
拉着他手,把他手指塞进我下边。
他不动。
装睡还是真累了?没劲。
我躺他旁边,迷迷糊糊也睡过去了。
————
他让我去医院戴个环儿,我忙不迭说好。
第二天是礼拜六,我起来就上了医院。
路上我还自我安慰呢,这不是为了他,这是为了我,为我的满足,为自我保护。
上了环儿,我更加有恃无恐,跟他在床上更没顾忌了。
可能我真有点儿上瘾了,感觉没法儿从这样的快感中抽身出来。
我越陷越深,越来越疯狂,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控制不住我的身体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的地步了,想停停不下来;肉体上的刺激越来越大,心理上的自责越来越小。
现在我觉得我是一正常人,比谁都正常。
我快乐,我健康,我能长寿。
寒假结束,他要回家了。
我上赶着给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大包小包。
我以为他得跟我依依不舍,得抱着我亲我,出门儿又回来,出门儿又回来,结果他拎上包儿就走,头也没回,连「再见」都没说。
我干了啥呀?我造了一孽。
大侄子走了。
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人。
我从厨走进卧、从卧走到厅。
只有这会儿,才觉出这独单挺大。
屋子里到处都留着我侄子的气味儿。
我贪婪地吸着,然后不知所措。
我从冰箱拿出那几条平鱼,摆餐桌上,安安静静闻那香味儿,享受那只属于我的快乐。
那几条平鱼已经没了生命,可腥味儿刺鼻。
我闻着闻着动了情,下身有了反应,湿了。
我拿起一条平鱼,鱼嘴对准我下边儿,开始摩擦。
鱼嘴凉凉的,冰得我不好受,可我停不下来。
我只想一件事儿——淫一下儿。
平鱼让我想起我哥嫂,想起他们送我侄子来那天。
我想起我侄子。
他在想我么?平鱼的腥味儿尤其刺激,对我来说就是春药,我一闻见下头就湿。
我狠狠手淫,淫到高潮,但不彻底。
我觉得空虚,哪儿哪儿都没力气,觉得活着没劲。
我走路轻飘飘,心情奇差,像做一大梦,像得一场大病。
我后悔。
后悔没用。
事儿已经出了。
我担心,怕他说出去。
怕也没用。
他是一混蛋。
我想他,想得不行。
他在干啥?准在想我,他那大鸡巴现在一准儿硬硬的。
我想上我哥家瞅瞅他,瞅一眼都行。
我穿上外衣,走到门口,拿起钥匙,又慢慢放下。
我不能去。
我是谁?我是他姑。
我上他家干啥去?打扰他?我不能。
再苦我也得咬牙忍。
我拚命忍啊。
这是纯粹煎熬。
姑姑去瞅瞅侄子,天经地义,怎么啦?我再次穿上外套。
我还是去了。
心跳。
手脚冰凉。
我哥家住平房,大杂院儿,院门儿朝东。
胡同挺窄,过俩夏利费点儿劲。
我站对面煤棚子,远远瞅着,不敢过去,又随时可能被发现。
他们家三口人谁都可能出来看见我,他们家邻居也进进出出,随时可能发现我,发现一个魂儿被拿住的女人,一个可怜的人,颠三倒四,魂不守舍,伤天害理,禽兽不如,彻底困惑,迷乱抓狂。
一旦发生关系,就整个都变了。
我这儿是干嘛呢我?有家不回、来哥这儿不敢进,快更年期了可干的事儿像青春期干的。
我不认识我了。
当年刚认识我前夫那会儿,我都没干过这么傻的事儿。
心脏狂蹦,快给我蹦死了。
这感觉我只有过一次,那是几十年前,我的初恋,事后证明初恋是无花果儿。
现在这感觉又来了,更强更猛。
我特激动,好像难得有机会重新活一回、又年轻一回。
我不敢承认,我怕,可事实摆这儿,我又动情了,这次是真爱,我投入了所有能投入的,爱的这个人是不能爱的又怎样?我就这样儿了。
那晚我在那煤棚子里一直戳到晚上十点,也没见着他。
他可能早睡了,或在外头疯。
我实在盯不住了,摇摇晃晃回了家。
洗了澡,上了床,盖被睡觉觉。
我该死,我有罪,我该下地狱。
以后怎办?不敢想。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都2012了,想那老多干啥?混呗。
其实人的所有烦恼,都来自于放不下。
只要把东西放下,就一点儿烦恼都没了。
我瞅野兽活挺好。
当你比野兽还野、比坏人还坏,你就不受伤害。
睡梦里,我在一监狱里,四周全是铁丝网铁栅栏门。
游泳池里,俩姑娘在水面接吻。
远处几个女的在抢皮球,黑白花的球落了水,一个姑娘紧跟着跳下水,可抱上来的却是一头黑白花奶牛。
我问身边一个满脸褶子的女人:「老大,我啥时能出去?」老女人瞅瞅我,慢悠悠说:「四十年。
」
【完】
侄子比我小26岁。
莫非我有潜在的儿子情结?可我跟儿子挺疏远,儿子跟我也不亲。
难道正因为这个所以我格外喜欢年轻小伙子?
我亏欠我儿子太多?
也许我用我侄子补偿我儿子?还债?
我侄子22岁,是我亲侄子。
我们两家儿离得远,来往不多,逢年过节串串,送个点心匣子,喝杯茶,也就这样。
每年我哥给我送一袋米,觉得我一个女人过日子不易,买大米吃力,我感谢他。
其实我离婚17年下来,大白菜,换灯泡,什么事儿都自己扛。
今年元旦,他们全家忽然来我这儿,带了好多苹果、橙子,还有六条平鱼,得五十多一斤,我从来都舍不得买,顶多在超市水产柜台,弯着腰近距离一眼一眼观察。
现在我一眼一眼打量我侄子,我真不敢相信几年前那个小毛 孩子现在成大人了。
他长大了,变高了,大宽肩膀,模样挺俊。
我哥嫂跟我说,我侄子寒假上英语强化班,离我这儿近,腿着五分钟,离他们家太远,说在我这儿住成不成?
我说住呗,你们都来住才好呢。
他们走了,留下一兜子苹果、一兜橙子、六条平鱼,还一半大小子。
平鱼散发着腥气,鱼腥填满每一立方厘米。
现在孩子长得真好。
我在他这岁数要啥没啥。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可能吃的里头残留农药激素甲基汞啥忒多,催得这么结实这么老高。
十七年,我一人。
家里只有一张床,双人的,是离婚以后买的。
旧床折旧卖了,太多伤心故事。
当初买这双人床的时候还怕人说闲话,后来想开了,我该在乎谁?我这儿一年到头撑死了来几拨串门的?万一我要是找着合适的呢?带回来挤一小窄床?苦谁不能苦自己,穷谁不能穷教育。
还没黑,他就问:「姑,我睡哪儿?」我说睡床呗睡哪儿,你就跟我睡。
他瞅瞅我瞅瞅床,眼神怪怪的。
我也打起鼓。
他在我眼里永远是孩子,可现在他已经比我高出一头。
他是大男人么?不,还得算孩子。
我眼前站的这人到底是什么?装傻充愣的白面书生?还是一头性成熟的小牲口?
我一普通人,就住这么一套独单,44平。
14 岁,我有过旖旎梦想,我知道我长得不错,梦想中当然就更加柔美婀娜妩媚多情,是男的见着我都走不动道儿。
24岁,我有过远大目标,那会儿年轻。
谁没年轻过?34岁,我还不服呢,不信邪,正较劲。
到44岁,认命了。
其实我一直特清楚,我知道我的命运不该这样,可偏偏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男人被小妖精勾走了,儿子也不跟我,存摺里那点儿盒儿钱一般不动,每天上班累得要死,长相也靠不住,不敢照镜子了。
离了以后找过几个,都不中意。
心灰意冷。
我这辈子就这么着啦。
现在大侄子进了门儿,我也就是灵光一闪,马上就笑话我自己:都徐娘了还自作多情,再说了,这是带血缘的,砸断骨头连着筋。
瞎打啥鼓?碎觉碎觉。
彻底黑了,也熬困了。
第二天我得上班他得上学。
我叫他先去洗,他叫我先洗。
洗就洗。
我脱掉毛衣,进了卫生间,脱了套头衫搭钩子上,回头瞅瞅门。
一人十七年,十七年安静过活,洗澡撒尿没关过门,没必要嘛,给谁关外头?可现在不一样,一男的就在我浴室门口儿转磨,像憋了八斤屎。
我当姑姑的,洗澡不关门,不合适;关吧,又疏远了。
我这是防谁呢?摆明防他。
他那么可怕么?
本来没事儿,我这儿喀啦一拉门儿,等于暗示他:这儿一女的啊,记住喽,你是男的。
本来无一物,强化惹尘埃。
等裤衩儿脱了,浑身光溜溜,我实在没勇气再敞着浴室门了。
我尽量不出声儿地拉上一半儿门。
拧开花洒,温水喷淋。
今儿我奶头儿怎这老敏感这老硬?外头,我大侄子已经比我前夫还高还壮了。
我倒是一直喜欢高大威猛型儿的男的,大宽肩膀,大硬胸肌,下边也大大的硬硬的顸顸的,能给我顶得魂飞魄散内种。
我哥嫂明知道我这儿就一张床,还把我侄子送过来,是真天真?还是考验我?还是心照不宣给我送个杀痒大礼包?
越想奶头儿越硬,越想下边越酸,恨不能手指头伸进去通一通。
忍啊忍,我还是忍住了。
浴室门毕竟没拉严。
我一大半的心思都盯着门口、悬在门外。
我早想好了,只要他进来,说要撒尿,我就,我就,我就一把薅住他,让他尿我里头。
这想法儿让我脸蛋儿焦红。
我居然这么淫荡对我大侄子想入非非?
就这样,心扑通扑通,他一直没进来,我澡也没冲好。
八成儿他比我难熬。
我的动物性本能占据上风,命令我的手指来到屄豆上轻轻按摩。
快感呈几何爆炸递增。
屄豆已经肿胀,饱满充血,赛开心果。
我这豆还从来没胀到过这个程度。
我真是骚得可以?揉搓不到二十下,我已经听不见水流声。
再揉两下我就能完蛋。
我的身体我熟悉。
这么些年来,每月总有固定减压时刻。
我想要的节奏、我喜欢的频率、我偏好的部位、时间火候,没人比我烂熟。
可偏偏就这两下,我没下手。
我给谁留着?给他?当时来不及深究,关水、擦乾,裹浴袍出来,脸蛋粉红,气喘吁吁。
电视哗哗开着,客厅没人。
我裹着浴袍光着脚走进卧室,还是空的。
走进厨房,也是空的。
邪门儿啦。
啥情况?忽然窗帘一动,一人闪出,满脸通红,是我侄子。
我想起,阳台通浴室窗。
我刚才冲澡他都看见了。
我正想发作,他噌一下蹿过来给我抱住,他胳膊钳着我所有的肉,强悍有力。
我还没挣开,他的嘴已经亲上我的嘴,我喊出的话全被他嘬进肺。
我闻他身上好像总是飘出平鱼的腥气,挺硬内种腥,贼腥。
我对气味天生敏感,加上这些年一人过惯了,过独了,刁了,不能容人了。
我使劲儿推他,他不松口儿。
我玩儿命跺他脚,他不放我。
我再推他,忽然感觉屄屄被他一把兜住,我浑身的力气一下都被泄掉了。
他的手指不停地摩擦我的下体,当时我就懵了。
我心理防线本来就弱,他这么一弄,我归零,心理防线全线垮塌,全投降,全敞开,然后就是很久没享受过的快感。
我很冲动。
我出格了。
我知道每个游戏都有规则,我违背了游戏规则,可我此刻特舒服,太舒服,我不想停。
我大侄子在奸我,可我没力气反击他。
是真的没力气。
洗完澡本来就浑身轻飘飘,动情大穴又被钳住,加上本来就在幻想被侵犯,所以过场走完,身子立刻软掉,比棉花都软,搂着他的粗脖子,半睁着眼,期待地等着下一步进犯。
这时他眼神沉着镇定,下边的手法异常精准,招招击中女人的中心。
这让我震惊:我碰到老手啦?
看看他,这么稚嫩,怎么会是老手?上唇胡须软软的,尖端变细,淡棕色,应该还没剃过;说话bia-bia 的,嗓子正倒仓,他能弄过多少姑娘?可他现在偏偏弄得我要死不活。
我浑身发烫,尤其后脑发热。
我把一切礼教所有教条啦弟子规啦多少孝多少贞啦统统Shift+Delete…我专心享受他的舌头他的手指。
男人的舌头男人的手指。
十秒不到,我就发现我已经疯了似的往上挺着腰,哭着高了。
我没哭我的命,没哭我的苦。
纯粹就一生理反应。
太强了,受不了,不适应。
来太晚了。
早点儿多好?还有就是,怎偏偏是他!我们以后咋整?
刚从被他指奸的虚脱里清醒过来点儿,冷不丁觉得屄门被扒开,一条大的、热的、粗的、硬硬的东西顶进来了。
硬硬的东西插进了我的身体,我都这岁数了,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我赶紧闭上眼睛,学鸵鸟。
我不敢睁开。
黑暗里,我知道我的脸被捧住,那双手强有力,呼吸带鱼腥。
我知道我被肏得快死,奶子狂飞,跟白痴似的。
我知道我的宫颈口被那条滚烫的东西冲撞着,快感越来越密集地冲撞我的丘脑。
我知道我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享受过这种快活了。
我咬着牙,不松开,正像不敢松开我的眼皮。
这一刻,我要深深沉浸在动物界的快活里头,加入野生动物的节日。
耳边是咆哮的喘息,是白热化拉风箱,振聋发聩,烈焰蒸腾。
这完全是成年男的喘息,粗野混帐,兽性十足。
我屄里夹着一条硬鸡,野蛮活塞,力拔山河,拖浆带水,泛着泡沫。
这鸡巴年纪轻轻,跟我还沾亲带故,我不该放他进来,我不该继续。
我心说,这是乱伦,乱搞,乱来,乱套,我也想提醒他,可我张不开嘴。
我又闻见他身上的平鱼的腥味儿,闻时间长了适应了,觉得也挺好闻的。
好比常年浸淫墨汁,久闻不觉其臭,反觉「书香」。
你要是养过马,时间长了会喜欢上马,包括身上的马味儿,马的肌肉,马的耸动,马的声音,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你的生命跟马融为一体。
烈马大展宏图,在我身上撒欢儿。
我应该推开他,立刻推开他,无条件推开他,可我浑身软绵绵,都快化了;胳膊倒有把劲儿,却搂着烈马脖子,死死钳住。
我舍不得清醒、舍不得让他停。
他完全是报复性地在我肉里发泄,顶撞,征服,弄得我生疼,感觉他对女人有仇,不共戴天。
忽然我的两条胳膊被他举过头顶,我的胳肢窝被热热的狗嘴亲着。
钻心的痒让我浑身扭动,像蛇一样。
即使这样,我还是舍不得睁开眼睛。
所有的罪孽都来吧,来吃我吧,吃吧,孩子,管够。
狗嘴唇狗舌头对我痒痒大穴的舔弄贪婪凶残令人发指,狗鸡巴对我下头的顶撞蛮横无理穷凶极恶,这混合型刺激超过了我承受极限。
在狂笑中痉挛,在痉挛中高潮,高潮中下头一热。
括约肌背叛了我。
我尿了,还没少尿。
也可能是sis朋友们老说的「喷」了。
当时已经停不下来,身体完全不由我控制,各肌肉群组强有力收缩,阴道的痉挛和尿都停不了。
尿尿呗。
放纵自己。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两胳膊上举被侄子按枕头上、胳肢窝被侄子亲着舔着,下头被侄子肏得哗哗喷尿、湿透被缛。
潮头过去,我浑身没劲儿,劲儿全被烈马卸掉。
多年前跟前夫苦苦博弈,最后完败,我以为我的心早死了,热情已被耗尽。
没想到我又活过来了。
我从心里感谢我侄子,这个年轻男人,他给了我新生。
我涌起一股激情,想为他做任何事儿,满足他、留住他,让他开心,让他永远属于我。
他干一会儿就拔出去,给我换一姿势,继续调情调戏,等我实在受不了,他才进来,狠狠给我杀痒。
他掌控全局,从容自信,动作到位,沉稳老辣,节奏跌宕,大开大阖,放得开,收得拢,张驰有度,行云流水。
他像贝多芬,像上帝。
他的岁数完全不匹配他的老练,这种老练完全是多年浸泡流水线的熟练工人。
现在的小年轻儿都这么早熟?还是叫我赶上一特例?
一直到听见也不谁肚子叫,才意识到都饿了。
一瞅,已经后半夜。
我下床洗手,去弄吃的,精力充沛,走路噔噔的,眼睛发亮,不困,一边儿做还一边儿唱呢——说天亲,天可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
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 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
说爹妈亲,爹妈可不算亲,爹妈不能永生存。
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一捧黄土雨泪纷纷。
说儿子亲,儿子不算亲,人留后代草留根。
八抬大轿把媳妇娶,儿子送给老丈人。
说亲戚亲,亲戚可不算亲,你有我富才算亲。
有朝一日这日子过穷了,富者不登穷家的门。
说朋友亲,朋友可不算亲,朋友本是陌路人。
人心不足蛇吞象,朋友翻脸就是仇人。
说闺蜜亲,闺蜜可不算亲,处心积虑套你隐私。
一旦触及她的利益,闺蜜翻脸就不认人。
说丈夫亲,丈夫可不算亲,背着你在外边找情人。
沾花惹草种下孽,死心塌地闹离婚。
说同行亲,同行可不算亲,勾心斗角好寒心 名夺利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
要说亲,大侄子最亲,侄子跟我心连着心。
轻拢慢捻抹复挑,跟我是砸断骨头连着筋。
夜宵做好了,汤汤水水,热气腾腾,跟他一起吃。
饿得透,吃得香,越吃越想吃。
一边吃一边瞅他,觉得他是这么精神,这么好。
我像花痴一样看他,像白痴一样说着大胆的话。
那些话我从来没说过,跟我前夫都没说过。
我整个儿换了一人。
他偶尔抬头,说我脸色儿好。
我得意半天,说都是他给我滋润的。
我怕他累着,我已经开始盘算明天下班路上去买一只三黄鸡回来给他好好补补。
吃完想起他还没射,上床再战,添酒回灯重开宴。
他提出要插我嘴,我忙不迭答应,然后张开嘴瞅着他。
我从来没让人插过嘴,前夫没这要求,我也不知道还能这么玩儿。
侄子过来了,近了,更近了,他那大东西直挺挺,大炮口儿挂着长长亮丝儿,炮口对着我眼睛,感觉好像要戳我眼眶子里。
我一点儿不怕,眼皮都没眨。
如果他真想戳我眼眶子,我就让他戳。
人有时候吧,真能涌起雄壮的英雄主义。
他身上那股腥味儿,怎么就让我迷醉?可能气味儿能给我催眠。
人陷进某种特定情境里头,就能鬼打墙,你就出不来,被障住,被魇住,多巴胺内啡肽或者别的胺别的肽还有大脑神经元、递质和受体、神经通路所有因素共同作用,你就能干出疯狂的事儿,比如逼急了打急了顶到那儿了,就真能自己走向铡刀、枪眼、火刑柱。
大炮捅进来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要吐,刚吃的那些全在嗓子眼儿那儿翻腾,争先恐后要喷出来。
提醒sis 的朋友们,插嘴这活儿,真不适合饭后。
说白了嘴就不是让插的家伙,嘴就是吃饭的家伙,亲嘴用还成,那老长那老顸一棍子戳你嘴里你自己试试啥感觉。
当时他身上的气味儿他蛋蛋的气味儿他大炮的气味儿,有腹股沟捂出来的汗味儿,汗可以是又臭又香的,有雄性激素睾丸酮,有蛋白质的清香,有肉香,还有一点儿味精那种鲜香,合在一起,浓浓的,腥腥的,香香的,臭臭的,单宁丰富,馥郁芬芳,复杂混合,致幻催眠,让我魂不守舍,甚至帮我克服了呕吐反射机制。
我仰着脖子张大嘴巴,满眼是泪,望着国王,战神,我的魔鬼,让这魔鬼可劲儿往最深处弄。
其实呕吐反射是没法抗拒的。
等我回过神儿来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吐了N多车了,从下巴脖子到胸口肚子全是刚才吃进去的汤汤水水,奇怪的是我居然没觉得难受,也没觉得呕吐物难闻,可见催眠效果之狠。
我还在坚持叼他,而事实上我已经吐得稀里哗啦了。
呕吐物的气味儿好像也有催眠效果,跟「平儿鱼的腥味儿」混合之后,形成更好闻更富含营养的浓香。
魔鬼得寸进尺,插得越来越深,还按住我后脑勺,玩儿了命往我嗓子眼儿紧里头戳。
瞅他那架式他是打算一路顶进我胃小弯。
英雄主义能激发人类潜能、能创造世间奇蹟,真的,不蒙你。
在英雄主义顶撞下,我含下了他那大炮筒的四分之三,这已经是我能做的极限了。
他呼嗤带喘,搞得好像马上要给我啥恩赐,只是他的俩手攥我头发弄得我疼。
我居然也忍了,连连点头哈哈地吞他那东西。
胃里酸水儿就没断。
酸性口液从我下嘴唇流我下巴上,又从我下巴往下拉着长长的丝儿往下垂往下飘,一直到我小肚子上。
垂到我小肚子上的我自己的口液已经冰凉,不那么忒舒服,不过我的注意力全在钢炮上、在他的满足上。
我想的只有一件事儿:满足他。
听他的声儿,我猜他马上就要射了。
我要让他快活、让他得到最大的快乐。
我张大嘴,试着最大限度地敞开喉咙,让他的大鸡往里、往里。
鸡头已经侵犯到我从没被人侵犯过的深度,大夫的压舌片都没探过我这么深。
我一边儿被他搞喉咙一边失控地呕儿啊呕儿啊喀喀喀喀地往上乾呕。
当时我豁出去了,已经掫出来了,没货了,反正已经这样儿了,就这么下去得了。
我不停,我要让他不受打扰不被中断地享受极乐快活,也许他喜欢的恰恰是射在女人喷涌呕吐物的热热的嗓子眼儿里头?
我这辈子只喝过两次酒。
第一次是十九岁,夏天,跟一男生去一小酒馆,喝完难受死了,据说后来是被那男同学扛回我家的。
第二回是结婚,喝了几小口,高兴嘛,以为这辈子踏实了、有指望了。
结果呢?嘿!现在我想喝,不管是酒还是精。
我还从没喝过精呢。
啥口感?
他会觉得射我嘴里特豪迈吧?把姑姑征服,瞅着姑姑咽他精华,特变态吧?
我够淫荡吧?我是荡妇么?
大脑前额皮层一阵明显发热,脑袋瓜儿一片空白,失忆,失禁,失控,失掉所有的控。
我猜等我撒手人寰那个瞬间,差不多也这感觉,特温馨,特舒服,放松,放纵,松弛,撒手,轻飘飘,像泡温泉,像醉酒,云中漫步,吸了粉儿,飙车,狂怒,面对行刑的枪口,啥都无所谓了,肏你妈啥罪恶呀伦理呀下辈子吧,啊。
他忽然加快了整我嘴巴的节奏,呼哧带喘当中断断续续说:「姑,我要射你嘴里!」当时他已经快给我小舌头顶烂了,我含着他鸡巴、一劲儿点头。
我是真心希望他直接射我嘴里、射我嗓子眼儿里、射我胃小弯里。
我今生从没允许任何男的射我嘴里。
可我当时就那么想、那么渴望、渴望新的尝试、新的刺激、新的玩儿法,渴望更放荡、更淫荡。
可能是一种接近献身的轰轰烈烈的雄壮的什么精神在激励我,可能我被卓娅奶奶要么胡兰奶奶附了体了?反正我忽然特别特别冲动,心跳贼快,脑仁儿嗡嗡的,眼睛瞅啥都视野模糊内种。
他彻底加快了肏我嘴巴的频率,吭嗤吭嗤得越发不像人了,整个一疯子。
我在心里默念着:搞死我吧、搞死我吧。
我要牺牲、要sacrifice.这很神圣的,你知道么,为一信念、为一念头儿,后脑一热,啪叽就捅出顶天立地一事儿,瞬间挺伟大的,金陵十三钗那句 w ǒ-men dòu-k ì(我们都去)10620 ,那是英雄主义,以卵击石,纯傻屄。
他到最后没捅进我胃小弯,也没射我舌头上。
是我对他构不成足够刺激?他有别的打算?还是他嫌我已婚、而他没有婚史?我问了,他没说。
他再次撤出去,还硬梆梆,然后舔我肛门。
这又是我第一次体验,神奇怪异,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立起来了。
快感太强,没法忍受,男人还能对女人这么样?我前夫从来没舔过。
现在我侄子是纯为讨好我还是他真喜欢这样?他舌头在我肛门口游动,时软时硬,还往里头钻,钻得我整条消化道舒服到嗓子眼儿。
忽然感觉有东西进我阴道里了,是他手指头,在里头狠命鼓捣,像挖宝。
倒挺好受的,不同的快乐奇特混合,绞在一起,把我弄死。
我缩着脚趾缩着腰,又高潮了一回。
从坡顶下来,全散架了,脑子一片空白,满身大汗,撅屁股趴那儿,动不了窝儿。
敢情有这么多种玩儿法。
我之前几十年真是白活。
他的东西进来了,这次进的是不该进的地儿。
我腰被他攥着,排泄的地方被插着。
鼻子里填满平鱼那种腥味儿,浓烈刺鼻。
我撅着屁股,在做畜牲不如的事儿,可我这会儿正美,正酣。
我莺声燕语,一半是迎合他,一半是自发。
弄后边居然也能舒服,也能高。
我高了,不知道是他从后头隔着一层肉顶到我前边还是我后边的神经末梢也同样敏感。
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我美了,这是最主要的。
战神又战略后撤了,东西还硬着,到我脸上,散着香气,香香的,臭臭的,好比咸亨炸臭乾儿,又臭又香,韵味十足,回味无穷。
有人觉得香菇香,有人一口不吃。
有人喜欢榴莲,有人爱吃臭豆腐。
臭豆腐诱人之处正在于它香香的又臭臭的。
我那年去绍兴,刚一进咸亨酒店,就被浓郁的臭香味儿包裹,整个店包了一团云雾,我在云雾里走,跟梦似的,跟现在似的。
炸臭乾儿上来以后,第一口不适应,后来越嚼越有滋味,回味深厚,让人上瘾。
餐后出了店,觉得没过瘾,就找路边小摊,切小块扎细竹签上那种,瓦灰色儿,炸至灰黑,街灯下就白嘴儿吃,什么酱汁都不蘸,吃了一串又一串,诱人的臭香在身边弥漫,进到我身体里,就像现在。
现在,战神跪我脸边儿上,凶器指着我,分明跟交警似的。
我张开嘴,把长长的粗粗的臭乾儿迎进来,暖他,润他,舔乾净他,崇拜他。
他让我无数次高潮无数次美,他给了我一辈子都没体验过的快活。
凶器在我嘴里一直硬着,不撤。
不撤我就一直舔,让他捅,表示驯顺。
他这么老到,我忽然闪过一念头:他是魔鬼。
对自己太自律自控其实挺可怕的,跟机器似的。
算了一下,他已经弄了我十多个小时了,这超出我前夫干过我的长度总和。
我前夫每次顶多半分钟。
我问他难受不难受,他说还行。
你说他真是人吗?
我舔着刚弄过我后边的凶器,不觉得下贱下作,不觉得恶心,反而满心欢喜。
舔着舔着冷不丁清醒过来,自己吓一跳,吓一身汗。
现在这真是我么?我这是干吗呢?这不作践自己么?我是他姑姑,端庄得体,一向稳重,我这是毁我自己呢,天亮我怎见他?以后我怎面对我哥?不容我多想,下一个大浪劈头盖脸又砸下来,把我淹没,把我拖回无底深渊。
大粗硬家伙又闯进我下体。
我快活地坠落,重力加速度堕落,叫唤出更下贱的声音,干出更多不可思议的事儿来。
他带着我拉着我舔着我顶着我到了一仙境,这儿可能是性游戏能达到的至高境界。
不知道他什么感觉,反正我从来没上过这么高的地方。
说实话我前夫跟我做爱不多,他老说累老说累。
我是传统女人,哪儿好意思一二再再而三提要求?
累就养着呗,不做就不做。
我哪儿能跟荡妇似的没完没了求他。
可现在我迷糊了:莫非我还就一荡妇?闷骚了二十几年,强忍,欺骗所有人,欺骗我自己。
其实荡妇有啥不好?为自己活,为自己爽,真诚,不装屄,长寿,不遭雷劈。
我维护这个维护那个,到最后我的家呢?碎了,成了碎片儿,团不到一块儿;老公、儿子全跟我不一条心。
这么多年我正经得到啥了?就一小独单。
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可怜我,给我派一童男子儿来帮我、度我。
我要再不珍惜这机会,谁还老帮你?
我抓着他,死死箍着他,可是不敢看他。
他喷白烟冒热汽,混横不羁,气势汹汹,这是一头肏屄兽,把我变成淫水母。
我真的乾渴到极点了。
我好像在报复前夫,报复此前受过的所有的委屈不公,玩儿命补偿我自己。
他捅会儿舔会儿,冲我说着可怕的话。
我听着顺着答应着,闭上眼睛设想那些流氓事儿真发生。
他那家伙里头可能有骨头,要不然的话怎能一直不软?他的运动没有尽头没有终结,他热爱这运动。
他要不是我侄子该多好?无数次中场休息,喝水、撒尿、聊天。
我问他:「你嫌不嫌我老?」他说:「你不老啊。
我还就爱肏四十来岁的娘们。
」「为什么啊?」「骚哇。
四十多岁的那是真骚,放得开,真败火。
」「告诉我实话,你糟蹋过多少阿姨?」「没多少,也就三十来个吧。
什么叫糟蹋呀?我这叫助人为乐,替天行道。
」说完又扑上来跟我绝斗。
我俩像末世仇家,又像棋逢对手,网球名将,玩儿命对抽,一千回合,谁都不累,大汗淋漓,还乐在其中。
我这辈子没出过那么多汗。
真出透了,床单是湿的,枕巾湿了,褥子也湿了,哪儿哪儿全都是湿的。
有时候我能听见床腿儿床脚嘠吱嘎吱,楼下邻居准能听见。
听见就听见。
我为谁活?
为这个为那个都活大半辈子了,我都快绝经了我。
闭上眼睛勒死战神,嘠吱嘎吱又听不见了。
你在极乐瞬间,耳道是封闭的,眼睛也一样,跟许仙最后在金山寺似的,或者更高境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想都不想,顺其自然,归隐山林纵情嚎叫,心甘情愿沦落为兽。
忽然想哭。
这些年我过得太苦了。
我太委屈我自己了。
什么什么都我一个人,我太难了。
我深感自己渺小、无助,深感绝望、孤独。
偶尔想了,自己弄弄,完事儿以后更难过。
我不是开放型的女人,特别想的时候也有,一般就是每月倒霉之前那几天,生理的需要靠自慰解决。
弄,谁都会,杀痒的法儿谁都有,问题是,孤独是绝症,它这没治。
现在,为对抗孤独,我抱紧他,也让他抱;亲他,也让他亲,让他进,让他顶,让他使劲填充我,填满我,塞严空虚,好像这样儿我就不孤独了。
窗外泛起淡蓝色天光。
床上,一朵大花在哭着怒放,补偿迟到的享乐,补偿一切。
人太缺什么就会找机会恶补。
恶补总会过梭,会犯错误,矫枉过正,失去灵魂,找错对象,自取其辱。
我脑子里头乱了套,开了锅。
事儿出了,事儿是错的,我是长辈,我必须断。
可这东西能断得了么?以后我怎面对我哥?他会不会怀疑?会不会闻出蛛丝马迹?发生关系是大事,身体、想法、内分泌都剧变,地覆天翻。
我相信,发生过关系的人,身上会发出新的味儿,跟以前体香不一样,自己能闻出来。
别人,靠近的话也能闻出来。
我怎么遮掩?他回去住以后会不会说漏嘴?
我问他说不说梦话?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不说,还说他们知道就知道了,都是家里人,怕啥。
他这什么逻辑?这事儿寒碜,可千万不能说出去,跟谁也不能说。
在有的地方,我们这种得浸猪笼,或者被人用大石头砸死。
他还是满不在乎。
吃过早饭,他跟我说想接着干、不想上课。
我说不去就不去,但是不能再弄了,必须睡觉。
身子要紧,这么干谁受得了?他趴我身上鼓捣了一会儿,趴下头不动了。
我一瞅,着了。
我也困,可我得上班。
上着班,想着家里趴一美少年,我心里忽悠忽悠的。
我脚步发飘,嗓音都比从前好听了。
中间上厕所的时候,擦出好多好多黏液。
想起昨天夜里,我下头又痒痒了。
毒瘾发作,凶猛暴烈,你根本招架不住,你扛不过去,你只能顺着他。
手指滑进来,动着,脑袋里头一片温热,人事儿啥都不想,只惦记满足兽性。
解完了骚,提好裤子,对着镜子照,镜子里那女人满脸通红,嘴唇潮湿,妩媚招人,骚货一枚,闻着自己手指。
我已经馋成这样儿啦?我是罪人。
我后悔了,我不该由着他。
我必须弥补,可我洗得乾净么?我再也回不到我原来的形象,他也不。
我该怎办?从此将错就错、当他秘密情人?
或者跟我哥说、说我对他好、他也对我好、让我哥成全我们?对,我嫁给他就完了。
我们到别的地方,苏州吴江,嗯,我喜欢那地方,乾乾净净,人少,路宽,没人认识我们。
我彻底疯了。
一女人,都这岁数了,被搞了一宿,居然就能痴呆到这程度。
我要真说了,我哥非给我送疯人院去。
不行不行,不去疯人院,吴江也去不了,还是得断。
下班买了三黄鸡,买了菜,两大兜子,沉死我了。
回来进楼道拐角猛抬头撞见一邻居,认识,打招呼。
我一惊,浑身一激灵,三黄鸡好悬没掉地上,嘴也不利索,答非所问,慌慌张张,脸色都变了,赶紧低头上楼。
进了家,手麻,沉的,吓的。
他真没上课去,我进门的时候他刚起床。
我定定神儿,觉得邻居瞅不出来,应该也没闻出来。
洗洗手,煲上鸡,洗菜。
他过来蹭我,摸我,我板着脸装没事儿人,闷头做饭。
他手伸进我衣服,贴着肉弄我。
我说,「姑姑错了。
咱别这样儿。
」他跟没听见似的,嘴唇身子手脚全贴上来,十足的章鱼,你根本做不了饭。
奶头被他捻硬,下头被他鼓捣出水了,心长草了,装不下去了。
放下菜,转身拉他上了床。
那天的三黄鸡差点儿糊了锅。
我看他是那么好看,看着他我心里是这么激动,激动得快晕过去了。
我眯着眼,微笑着,什么都不用说,就很幸福,心里美。
我想要他,现在就要。
我居然成了痴女一枚。
性瘾不是病,发作真要命。
人狂怒的瞬间,智商是一;动情时刻,智商是零。
我彻底被魇住了,鬼上了身,我被附了体,心甘情愿沉沦变态,失掉理智判断,醒不过来,走不出来。
其实也不是肏屄带魔力,主要是高潮那几秒钟让人分泌特别的东西,比如多巴胺大爆发,大脑释放大量内啡肽,作用像吗啡,致幻剂。
我觉得,高潮就是毒品。
————
第二天他上课去了,临走在我身上腻不够,非逼我答应他晚上接着弄,不答应不走。
我心里热乎乎,幸福。
我喜欢被人需要、被人迷恋,喜欢有人跟我耍赖。
母性被激发出来,往外流,比奶浓。
我被自己感动了。
这毒狠毒就狠毒在,你粘上他之后,你能自己给自己催眠,你给自己找藉口找理由,你压根儿不觉得他有毒,你还帮他复制病毒。
我下班回家,做好饭,听见敲门了,他回来了。
我乐着蹦着颠着去开门,笑容呱叽僵住——他和一姑娘,拉着手进的屋,跟我说,「这是我们班的。
」我从头凉到脚。
女人做事情经常是糊涂的,反正我是这样儿,情商是变数,该高的时候偏偏低,发起烧倒是高高的。
高烧中,我被玩儿得晕晕的,以为他对我真有感情了,没想到他跟我压根儿就是去火,就纯发泄。
我忽然觉得他挺邪恶的,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坏?
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们俩,还陪着笑,故作轻松,偶尔出戏,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侄子是一恶魔,吃完就搂着那姑娘进了我的卧室,不关门,直接开练。
我百抓挠心,脸上发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们那淫声秽语像针往我心上扎,不听不行啊,这独单拢共就这么大,我往哪儿躲呀我?
我走进厨房,两米乘两米,狭窄的空间压迫着我,所有的东西,橱柜、刀具、菜板、水池、灶台、锅碗瓢盆筷子勺统统朝我压过来,想要压死我。
他们在干吗?
在我床上,在我刚享受到快乐的地方,在我的地盘折腾,他们用的什么姿势?
那女孩能比我强么?我没瞅出她哪儿比我好呀。
我侄子精神头儿够棒的,他就不累么?自打他来我这儿,他就一直在战斗,他简直超人呀。
冷不丁地,那姑娘蹿出来,尖叫着,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他追出来,把那姑娘按我地砖上。
俩人跟疯子似的折腾,一点儿羞耻感没有,整个原始人。
当然了,我还不如他们,我算什么?背德姑姑,禽兽不如。
我跟全世界宣了战,我干的事儿被全世界唾骂。
所有人都比我强、比我正常。
我终于清醒了,又好像更糊涂了,浑身皱巴,难受哇,心里头特别的难过,伤感,后悔,还不能自拔,思维跟瞎线团似的,把我绕里头,缠死,走不出来。
补习班儿刚认识一天,带我这儿就弄,也不怕得病?我关上厨房门,捂上耳朵,浑身哆嗦。
我这是怎么了?事情怎么会这样?生活本来好好的,平静如水,没灾没祸也就算是福了。
好端端的,我侄子闯进来,弄了我,我跟傻瓜似的动了情。
结果现在自作自受。
我应该把他撵出去,现在就去!
我昂首挺胸出了厨房,内俩已经回了我卧室,叽叽嘎嘎,嗨哟嗨哟。
我义正词严走进卧室,面对我侄子,问:「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侄子说:「过来抬她脚,给我抬高。
」我站床边儿助纣为虐,提起那姑娘脚腕子,用力往上抬,瞅着我侄子大粗家伙往人家眼儿里捅,近距离听着噗叽噗叽声。
那姑娘四仰八叉,任我侄子肆虐。
没想到近距离听这噗叽声催情作用这么大。
我下头酸痒难熬到了极限,我使劲夹着大腿,扭着腰腰。
我侄子发疯似的干着,忽然撤出鸡巴,指着那姑娘屄豆命令我说:「过来舔这儿。
」我中了邪似的爬过去,张嘴就亲,伸舌头就舔。
那姑娘酸酸的,有点儿咸,有点儿骺,有点儿腥,跟平鱼的腥还不一样。
我这辈子打死我都没想过舔女的,可我现在真的正在舔,十足卖力,而且沉醉其中,从女女舔盘子里头还品出了甜头品出醇香。
为什么非要把寻欢对象设成异性?
我一边舔盘子,我侄子一边在我后头舔我。
床上,我们像三条狗,转圈儿舔。
我一会儿是男的,一会儿是女的。
下头湿得不像话,空虚得紧,只盼谁来捅捅。
过了一会儿,恶魔让那姑娘趴我脸上,跟我69,他肏那姑娘,让我舔他蛋蛋。
他肏一会儿,拔出来让我舔一会儿。
我刚给他舔乾净,他又肏进去。
他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完全被致幻了的。
灵魂丢了,只剩一付皮囊。
行尸走肉。
逆来顺受。
痴呆女奴。
脑瘫女仆。
一使唤丫头。
我身体上离不开他,我求他弄我。
感情上更离不开他。
我满脑子想法,疯狂大胆,每一条都不敢说出来,我知道世道不容我。
在我眼前不到五厘米,恶魔的大粗鸡巴狠狠肏着刚认识的嫩货。
那货被肏美了,骚水儿狂滋,滋我一脸。
恶魔把她两条胳膊背后头绑起来,绑得紧,都勒紫了。
恶魔薅她头发接着肏她。
她惨叫着,哭喊着,不过在我听来她正享受。
我舔她屁眼儿、掐她骚豆。
我百般的曲意逢迎,可恶魔就是不干我。
送走那姑娘,我跟我侄子说:「她挺好的。
姑瞅你们交往姑特开心。
」他不搭理我,一边唱着「说天亲、天可不算亲」,一边进卫生间打开水冲澡。
我跟进卫生间,给他搓背,帮他洗乾净。
他的鸡巴一直立着,不倒。
洗完出来我说你刚才没射呀?你怎么打算?他趴床上不动了。
我下头难受死了。
拉着他手,把他手指塞进我下边。
他不动。
装睡还是真累了?没劲。
我躺他旁边,迷迷糊糊也睡过去了。
————
他让我去医院戴个环儿,我忙不迭说好。
第二天是礼拜六,我起来就上了医院。
路上我还自我安慰呢,这不是为了他,这是为了我,为我的满足,为自我保护。
上了环儿,我更加有恃无恐,跟他在床上更没顾忌了。
可能我真有点儿上瘾了,感觉没法儿从这样的快感中抽身出来。
我越陷越深,越来越疯狂,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控制不住我的身体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的地步了,想停停不下来;肉体上的刺激越来越大,心理上的自责越来越小。
现在我觉得我是一正常人,比谁都正常。
我快乐,我健康,我能长寿。
寒假结束,他要回家了。
我上赶着给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大包小包。
我以为他得跟我依依不舍,得抱着我亲我,出门儿又回来,出门儿又回来,结果他拎上包儿就走,头也没回,连「再见」都没说。
我干了啥呀?我造了一孽。
大侄子走了。
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人。
我从厨走进卧、从卧走到厅。
只有这会儿,才觉出这独单挺大。
屋子里到处都留着我侄子的气味儿。
我贪婪地吸着,然后不知所措。
我从冰箱拿出那几条平鱼,摆餐桌上,安安静静闻那香味儿,享受那只属于我的快乐。
那几条平鱼已经没了生命,可腥味儿刺鼻。
我闻着闻着动了情,下身有了反应,湿了。
我拿起一条平鱼,鱼嘴对准我下边儿,开始摩擦。
鱼嘴凉凉的,冰得我不好受,可我停不下来。
我只想一件事儿——淫一下儿。
平鱼让我想起我哥嫂,想起他们送我侄子来那天。
我想起我侄子。
他在想我么?平鱼的腥味儿尤其刺激,对我来说就是春药,我一闻见下头就湿。
我狠狠手淫,淫到高潮,但不彻底。
我觉得空虚,哪儿哪儿都没力气,觉得活着没劲。
我走路轻飘飘,心情奇差,像做一大梦,像得一场大病。
我后悔。
后悔没用。
事儿已经出了。
我担心,怕他说出去。
怕也没用。
他是一混蛋。
我想他,想得不行。
他在干啥?准在想我,他那大鸡巴现在一准儿硬硬的。
我想上我哥家瞅瞅他,瞅一眼都行。
我穿上外衣,走到门口,拿起钥匙,又慢慢放下。
我不能去。
我是谁?我是他姑。
我上他家干啥去?打扰他?我不能。
再苦我也得咬牙忍。
我拚命忍啊。
这是纯粹煎熬。
姑姑去瞅瞅侄子,天经地义,怎么啦?我再次穿上外套。
我还是去了。
心跳。
手脚冰凉。
我哥家住平房,大杂院儿,院门儿朝东。
胡同挺窄,过俩夏利费点儿劲。
我站对面煤棚子,远远瞅着,不敢过去,又随时可能被发现。
他们家三口人谁都可能出来看见我,他们家邻居也进进出出,随时可能发现我,发现一个魂儿被拿住的女人,一个可怜的人,颠三倒四,魂不守舍,伤天害理,禽兽不如,彻底困惑,迷乱抓狂。
一旦发生关系,就整个都变了。
我这儿是干嘛呢我?有家不回、来哥这儿不敢进,快更年期了可干的事儿像青春期干的。
我不认识我了。
当年刚认识我前夫那会儿,我都没干过这么傻的事儿。
心脏狂蹦,快给我蹦死了。
这感觉我只有过一次,那是几十年前,我的初恋,事后证明初恋是无花果儿。
现在这感觉又来了,更强更猛。
我特激动,好像难得有机会重新活一回、又年轻一回。
我不敢承认,我怕,可事实摆这儿,我又动情了,这次是真爱,我投入了所有能投入的,爱的这个人是不能爱的又怎样?我就这样儿了。
那晚我在那煤棚子里一直戳到晚上十点,也没见着他。
他可能早睡了,或在外头疯。
我实在盯不住了,摇摇晃晃回了家。
洗了澡,上了床,盖被睡觉觉。
我该死,我有罪,我该下地狱。
以后怎办?不敢想。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都2012了,想那老多干啥?混呗。
其实人的所有烦恼,都来自于放不下。
只要把东西放下,就一点儿烦恼都没了。
我瞅野兽活挺好。
当你比野兽还野、比坏人还坏,你就不受伤害。
睡梦里,我在一监狱里,四周全是铁丝网铁栅栏门。
游泳池里,俩姑娘在水面接吻。
远处几个女的在抢皮球,黑白花的球落了水,一个姑娘紧跟着跳下水,可抱上来的却是一头黑白花奶牛。
我问身边一个满脸褶子的女人:「老大,我啥时能出去?」老女人瞅瞅我,慢悠悠说:「四十年。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