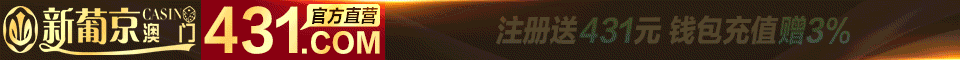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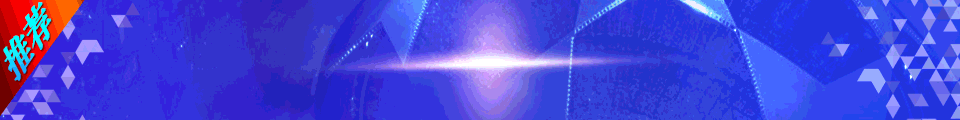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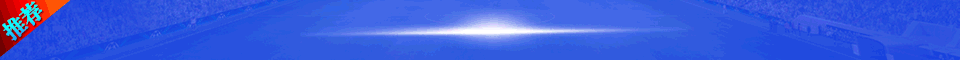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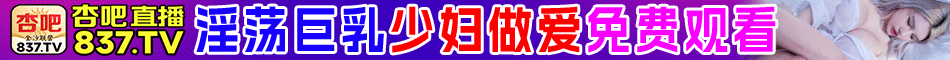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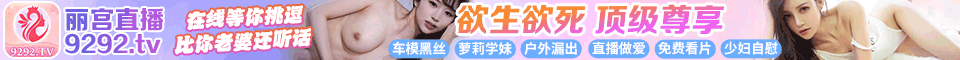
农村生活
黄花菜开始出骨朵,我知道麦子快收了。已经割了两年麦子,还割苜蓿,割草,我相信我有能力一个人割完。我太喜欢麦子面了,那么细,想起来都香。
有个老男人牵着一头高大的叫驴(公驴)来到我们庄上。那叫驴威风的很,只是屁股后面有个木头棒棒拖在尾巴下,走起来一挡一挡地。奶奶招呼他进来坐,说话抽旱烟,一会便指示我去牵来草驴(母驴)。那人挽起袖子,牵着他的叫驴在草驴屁股后转来转去,还不时用手在叫驴胯下又摸又拽。不多时,垂下一条粗长的东西,乌黑发亮。这时候,他便像小时候外公带我看的马戏表演一样,用手势指挥着叫驴,叫驴就跃起前蹄,跨上我家毛驴的后背。于是那人用手抓住那黑长物事,对准草驴屁股,一下像打针似得没了进去。
给人家牲口配一次种,要收半斗黄豆做报酬。不是没粮食吃了吗?怎么有这么好的黄豆?我想着炒上吃肯定很香。
星期天,我和姐姐一起去驮水,路上给她讲驴配种的事情。她说早见过,人也一样,只要男人的牛牛放进女人里面,再尿一泡尿,就可以怀上孩子。我说我拉着驴没看清楚,她就把驮水毛驴的尾巴拉起来给我看,我说和她的很像,她就打我,闹腾的把狗招惹来,追着我们一路跑下山去。
也就是在这天的晚上,我的牛牛硬了起来,而且放进了姐姐的痞里。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爬上去后放在她的腿缝里,磨了一会就感觉下面大了。她发觉不对,想摸,刚一抬屁股,我就觉得热热地进了一个东西里,弄的牛牛尖尖那地方还有点刺痛。她也急了,抽出一条腿弯曲着好象是要掀翻我,没想到进去的更多,疼的也更厉害,还涨的很。我很紧张,不知所措,而她却在用力往外抽另一条我压着的腿。我想我疼,她肯定也疼,赶紧侧着身子给她让,便从她身上掉下来。牛牛猛地从她痞里拉出来,舒服地使我打了个激灵。屁股那里开始跳动,连续的跳动,一股一股的东西冒出来,弄了她一肚子。
我吓坏了,姐姐也害怕,以为我尿她身上了,一顿猛掐,掀掉被子让我给她擦。我用手摸,粘糊糊的,更加害怕。突然,火柴划亮了,奶奶可怕的脸出现在光线中,而我的手还没来得及从她交裆里取开。
姐姐哭了,不知道为什么,边哭边骂我。我跳下炕没来及跑出去,只好光着身子跪在窑洞最里面,忍着疼让奶奶用擀面仗抽脊背。
奶奶病了,我去请「根子」来。看完病,奶奶给他讲我坏事,说我小小年纪,心眼坏透。我腿疼,有点瘸,拐着进去拿镰刀,奶奶指着我给「根子」说:「你看,才多高点,你说你这么大点知道啥?他就知道弄她姐姐,他姐姐睡着了,他就弄,也不知道谁教的,你说他爸妈能是好东西吗,他们家有好东西吗?……」。
我不能在屋里睡觉了,奶奶找了块破席,我拿到牲口窑里铺在一头塌了坑的炕上睡。晚上冷的很,就爬进牲口槽里,用被子裹着比炕上暖和。好在毛驴经常不卧倒,我能伸手就摸到它的头,不太害怕,睡得也香。
好象村里人都知道我晚上偷着叠姐姐,脸烧又躲不过,姐姐还天天骂我。没有办法,我就早起,天亮前就把水驮回来,然后出去田里干活,不是割草就是锄地,直到中午才回来,吃完饭赶着羊出门,躲到沟里自由幻想。
又开始割麦子了,姐姐已经放假,但她不理我,骂我是「流氓」,说的很恶毒。我担心继父回来知道,但他没回来割麦子,因为我割起来比大人都快。在黄橙橙的麦田里,我弓着腰能从早上割到天黑。去年腰疼,今年刚开始也疼,但几天下来就没感觉了。习惯后,连驮水走路都弓着腰,奶奶骂我是小老头,死起赖海(音,骂人的)。
碾麦子是技术活,奶奶怕我不会赶驴,碾子压不均匀,碾不干净,就想找人帮忙。刚好「根子」在里庄给我二嫂看完病路过,听奶奶说起,便答应帮忙。
中午吃完饭开始,晚上吃饭前就碾完了。吃饭的时候,他看着姐姐说她脸色不好,然后抽着旱烟满院子乱转,最后说有鬼进家了,要给姐姐驱一驱。奶奶吓的脸色都变了,掏出两块钱央求他看。于是他把姐姐弄到小窑洞的炕上,就把奶奶赶出来并把门顶了。我在院子里收麦草,听得里面大声的念咒,一直念,姐姐也有声音,但被念咒声压住。弄了半天,门开了,他在炕头抽烟,姐姐走出来回了灶方窑,脸色红润,真的好象不如以前苍白。奶奶高兴地给「根子」装了些新麦子,送他走了。
把麦子扬干净(扬起来,借着风吹去麦壳,只剩颗粒)装起来,比往年多了些,我很高兴,奶奶也高兴。接下来可以休息一阵,但我家人丁少,我便比别人家更早地开始犁地,准备种秋(播种秋天的种子)。
前几天一直下雨,今天晴了,我赶紧套好牲口扛着犁去了田埂。因为太早,整个山野间就我吆喝着一对毛驴。中午我带了粗面馒头,就在田埂地头吃了。吃完继续犁,有快石头拌住,把犁把折断了。没有办法,只好收工。
中午的太阳毒的很,晒得我又累又渴。平常我把犁和东西让一头驴驮着,自己骑一头,可现在草驴的肚子已经开始大起来,我不敢让它驮,也不敢骑,只好走回来。
在院子口,我卸下犁放在柴草堆边,把驴放了在周围吃草。院子里静悄悄地,奶奶和姐姐好象都不在家。狗温顺地过来舔我,跟着我进了屋。喝完一大勺水,出来蹲到门槛上抽旱烟。我没有旱烟,是五爷偷偷给我的,只有奶奶不再才敢这样抽,平常都在外面抽。
突然牲口窑里好象有声音,那里是我的地方。有我借的小说呢,别被人偷了。
赶紧走过去,快到门口,就听见姐姐的哼哼声音,好象很难受。不会又病了吧?
正想进去,却听见里庄碎哥的说话声:「美吗?美不美?」姐姐答应着,声音很含糊,夹杂着别的声音。我把旱烟灭了,抬起脚轻轻过去,把头从半掩的门缝里探进去。只见炕后的草料堆里,碎哥白白的屁股压在姐姐身上,黑黑的牛牛有半截扎在姐姐肉里。
我惊呆了,热血一下升上心头,难受地天旋地转。
姐姐看见我了,碎哥也爬起来,于是姐姐很白的奶头出现在眼前,比新面做的馒头还白。我更加难受,憋的脸红脖子粗,大口地喘气。
碎哥骂我出去,过来关门。姐姐也过来,光光地拉住我拐进磨窑(磨小麦面的窑洞),对我说:「不能告诉奶奶啊,不能告诉谁,完了我让你也弄一下,你先出去……」我虽然以前老摸她,老弄她,但从没这样在大白天见过她的奶头,眼睛都直了,觉得那么好看,那么美,连她说什么也没听见,最后只听到「你先出去给我看人,有人来就喊我。」便回头就跑。
蹲在柴草堆旁,手抖地连旱烟都卷不起来。站起来,一低头,看见裤裆里竖的老高。我已经很久没有裤衩穿了,裤带是根绳子,扎起来就把宽大的裤子拉斜系着,这样竖起来,裤裆那里特别难看。
一会儿碎哥出来了,过来蹲着要我烟,我说没有,他说不要给人说,要不就告我抽旱烟,还告我偷他家的土瓜。我点头答应,给他旱烟,他卷了一根点着抽上走了。
姐姐从我的牲口窑里出来,穿的整整齐齐,有后母那么洋气,只是头发有些乱,径直进了灶方窑。我望着窑口,外面阳光刺眼,里面却黑洞洞的看不见人影。
正瞅着,她出来门口,招手叫我。赶紧起来,边拍屁股上的土边小跑着过去。
她坐在门槛上梳头,我蹲在她跟前。她很好看,干净的很,我却是这么脏,破烂的像个什么,于是自惭的不敢看她。她歪过脑袋,脸红红的,问我刚才看到没有。我垂着脑袋点点头,听见她「咯咯」地笑起来。笑毕,她问道:「你能竖起来吗?」我又点点头。半天没有声音,我偷眼看她,发现她正看我,有些不相信的样子。
狗摇着尾巴跑出去了,我站起来向凹坡上看去,奶奶迈着小碎步正往下走来。
姐姐也看见了,给我说:「记住啊,不要说,要不然不理你。」奶奶在门口看见旱烟把子,我只抽了半根,烟把子一般不扔,都装起来,弄碎和在烟里继续卷,那个肯定不是我扔的。但奶奶就看我,我急了说碎哥前面过来了。姐姐在奶奶身后给我猛使眼色,我知道露嘴了,结巴着不知道说什么。姐姐编慌说:「他来借煤油,我没给,就走了」。晚上奶奶进去给大妈家还钱,姐姐拉我到牲口窑里,又掐又拧,说我是故意的。我解释不是,是忘记了,她就脱了裤子,让我弄她,说我弄了就不故意了。
我抱了些干草放在门槛里,她说这里能听到外面,万一奶奶回来就知道。我脱了裤子爬上去,但牛牛没有竖起来。姐姐说我不行,没长大,不要再弄了。我说想摸她奶头,她不同意,说我手脏,弄脏了她衣服。我喜欢她的奶头,就结巴着央求,最后她掀起来让我摸。手刚搭上,感觉牛牛就大了,往她交裆里钻。
姐姐感觉到我牛牛大了,就想把我压着的腿抽出来,可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反倒骑着往她腿缝里顶。她骂我,说我蠢的要死,使劲拧我胳膊上的肉。我疼地跳起来,才发现她叉开了腿,招手叫我爬上去。
她把手伸到下面,抓住我的牛牛对准一个地方,拉我屁股让我叠。我很着急,心跳的厉害,但怕她没有洞洞,弄疼她。她不耐烦的很,用两只手抱住我屁股往下拉,一下就把牛牛弄进她疲里。里面就像个鸡窝,热呼呼的,舒服的很。她让我抬屁股上下动,我照做,越加舒服,连续这样着,牛牛就摩擦地发疼。想取出来,但还舒服着,又舍不得,便忍着疼继续那样弄。姐姐哼哼着,我问她,她说是舒服地哼哼。于是我也学碎哥的话说:「美不美?」她说:「美」,就感觉她抱我抱得更紧了。
突然,牛牛头那儿,就是尿尿的地方,猛的一阵剧疼,好象皮被撕破了。我想爬起来,但她抱着我腰,起不来,屁股后面又开始抽动,一跳一跳地往里面冒尿。
我喊:「我尿里面了,快松开」,她也感觉到了,但不松,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等我尿完。
离开她后,我对着外面的光线看,牛牛的包皮被翻到后面,发红的头头完全露在外面,似乎有些肿,我想可能叠活了就变成这样了。姐姐穿裤子,穿好就打我,边打边拧,说我冒她里面,要怀小孩就让奶奶打死我。我赶紧跑出院子,远远地蹲着看。夜色已经降下来,远处的山峦开始模糊起来。
【完】
有个老男人牵着一头高大的叫驴(公驴)来到我们庄上。那叫驴威风的很,只是屁股后面有个木头棒棒拖在尾巴下,走起来一挡一挡地。奶奶招呼他进来坐,说话抽旱烟,一会便指示我去牵来草驴(母驴)。那人挽起袖子,牵着他的叫驴在草驴屁股后转来转去,还不时用手在叫驴胯下又摸又拽。不多时,垂下一条粗长的东西,乌黑发亮。这时候,他便像小时候外公带我看的马戏表演一样,用手势指挥着叫驴,叫驴就跃起前蹄,跨上我家毛驴的后背。于是那人用手抓住那黑长物事,对准草驴屁股,一下像打针似得没了进去。
给人家牲口配一次种,要收半斗黄豆做报酬。不是没粮食吃了吗?怎么有这么好的黄豆?我想着炒上吃肯定很香。
星期天,我和姐姐一起去驮水,路上给她讲驴配种的事情。她说早见过,人也一样,只要男人的牛牛放进女人里面,再尿一泡尿,就可以怀上孩子。我说我拉着驴没看清楚,她就把驮水毛驴的尾巴拉起来给我看,我说和她的很像,她就打我,闹腾的把狗招惹来,追着我们一路跑下山去。
也就是在这天的晚上,我的牛牛硬了起来,而且放进了姐姐的痞里。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爬上去后放在她的腿缝里,磨了一会就感觉下面大了。她发觉不对,想摸,刚一抬屁股,我就觉得热热地进了一个东西里,弄的牛牛尖尖那地方还有点刺痛。她也急了,抽出一条腿弯曲着好象是要掀翻我,没想到进去的更多,疼的也更厉害,还涨的很。我很紧张,不知所措,而她却在用力往外抽另一条我压着的腿。我想我疼,她肯定也疼,赶紧侧着身子给她让,便从她身上掉下来。牛牛猛地从她痞里拉出来,舒服地使我打了个激灵。屁股那里开始跳动,连续的跳动,一股一股的东西冒出来,弄了她一肚子。
我吓坏了,姐姐也害怕,以为我尿她身上了,一顿猛掐,掀掉被子让我给她擦。我用手摸,粘糊糊的,更加害怕。突然,火柴划亮了,奶奶可怕的脸出现在光线中,而我的手还没来得及从她交裆里取开。
姐姐哭了,不知道为什么,边哭边骂我。我跳下炕没来及跑出去,只好光着身子跪在窑洞最里面,忍着疼让奶奶用擀面仗抽脊背。
奶奶病了,我去请「根子」来。看完病,奶奶给他讲我坏事,说我小小年纪,心眼坏透。我腿疼,有点瘸,拐着进去拿镰刀,奶奶指着我给「根子」说:「你看,才多高点,你说你这么大点知道啥?他就知道弄她姐姐,他姐姐睡着了,他就弄,也不知道谁教的,你说他爸妈能是好东西吗,他们家有好东西吗?……」。
我不能在屋里睡觉了,奶奶找了块破席,我拿到牲口窑里铺在一头塌了坑的炕上睡。晚上冷的很,就爬进牲口槽里,用被子裹着比炕上暖和。好在毛驴经常不卧倒,我能伸手就摸到它的头,不太害怕,睡得也香。
好象村里人都知道我晚上偷着叠姐姐,脸烧又躲不过,姐姐还天天骂我。没有办法,我就早起,天亮前就把水驮回来,然后出去田里干活,不是割草就是锄地,直到中午才回来,吃完饭赶着羊出门,躲到沟里自由幻想。
又开始割麦子了,姐姐已经放假,但她不理我,骂我是「流氓」,说的很恶毒。我担心继父回来知道,但他没回来割麦子,因为我割起来比大人都快。在黄橙橙的麦田里,我弓着腰能从早上割到天黑。去年腰疼,今年刚开始也疼,但几天下来就没感觉了。习惯后,连驮水走路都弓着腰,奶奶骂我是小老头,死起赖海(音,骂人的)。
碾麦子是技术活,奶奶怕我不会赶驴,碾子压不均匀,碾不干净,就想找人帮忙。刚好「根子」在里庄给我二嫂看完病路过,听奶奶说起,便答应帮忙。
中午吃完饭开始,晚上吃饭前就碾完了。吃饭的时候,他看着姐姐说她脸色不好,然后抽着旱烟满院子乱转,最后说有鬼进家了,要给姐姐驱一驱。奶奶吓的脸色都变了,掏出两块钱央求他看。于是他把姐姐弄到小窑洞的炕上,就把奶奶赶出来并把门顶了。我在院子里收麦草,听得里面大声的念咒,一直念,姐姐也有声音,但被念咒声压住。弄了半天,门开了,他在炕头抽烟,姐姐走出来回了灶方窑,脸色红润,真的好象不如以前苍白。奶奶高兴地给「根子」装了些新麦子,送他走了。
把麦子扬干净(扬起来,借着风吹去麦壳,只剩颗粒)装起来,比往年多了些,我很高兴,奶奶也高兴。接下来可以休息一阵,但我家人丁少,我便比别人家更早地开始犁地,准备种秋(播种秋天的种子)。
前几天一直下雨,今天晴了,我赶紧套好牲口扛着犁去了田埂。因为太早,整个山野间就我吆喝着一对毛驴。中午我带了粗面馒头,就在田埂地头吃了。吃完继续犁,有快石头拌住,把犁把折断了。没有办法,只好收工。
中午的太阳毒的很,晒得我又累又渴。平常我把犁和东西让一头驴驮着,自己骑一头,可现在草驴的肚子已经开始大起来,我不敢让它驮,也不敢骑,只好走回来。
在院子口,我卸下犁放在柴草堆边,把驴放了在周围吃草。院子里静悄悄地,奶奶和姐姐好象都不在家。狗温顺地过来舔我,跟着我进了屋。喝完一大勺水,出来蹲到门槛上抽旱烟。我没有旱烟,是五爷偷偷给我的,只有奶奶不再才敢这样抽,平常都在外面抽。
突然牲口窑里好象有声音,那里是我的地方。有我借的小说呢,别被人偷了。
赶紧走过去,快到门口,就听见姐姐的哼哼声音,好象很难受。不会又病了吧?
正想进去,却听见里庄碎哥的说话声:「美吗?美不美?」姐姐答应着,声音很含糊,夹杂着别的声音。我把旱烟灭了,抬起脚轻轻过去,把头从半掩的门缝里探进去。只见炕后的草料堆里,碎哥白白的屁股压在姐姐身上,黑黑的牛牛有半截扎在姐姐肉里。
我惊呆了,热血一下升上心头,难受地天旋地转。
姐姐看见我了,碎哥也爬起来,于是姐姐很白的奶头出现在眼前,比新面做的馒头还白。我更加难受,憋的脸红脖子粗,大口地喘气。
碎哥骂我出去,过来关门。姐姐也过来,光光地拉住我拐进磨窑(磨小麦面的窑洞),对我说:「不能告诉奶奶啊,不能告诉谁,完了我让你也弄一下,你先出去……」我虽然以前老摸她,老弄她,但从没这样在大白天见过她的奶头,眼睛都直了,觉得那么好看,那么美,连她说什么也没听见,最后只听到「你先出去给我看人,有人来就喊我。」便回头就跑。
蹲在柴草堆旁,手抖地连旱烟都卷不起来。站起来,一低头,看见裤裆里竖的老高。我已经很久没有裤衩穿了,裤带是根绳子,扎起来就把宽大的裤子拉斜系着,这样竖起来,裤裆那里特别难看。
一会儿碎哥出来了,过来蹲着要我烟,我说没有,他说不要给人说,要不就告我抽旱烟,还告我偷他家的土瓜。我点头答应,给他旱烟,他卷了一根点着抽上走了。
姐姐从我的牲口窑里出来,穿的整整齐齐,有后母那么洋气,只是头发有些乱,径直进了灶方窑。我望着窑口,外面阳光刺眼,里面却黑洞洞的看不见人影。
正瞅着,她出来门口,招手叫我。赶紧起来,边拍屁股上的土边小跑着过去。
她坐在门槛上梳头,我蹲在她跟前。她很好看,干净的很,我却是这么脏,破烂的像个什么,于是自惭的不敢看她。她歪过脑袋,脸红红的,问我刚才看到没有。我垂着脑袋点点头,听见她「咯咯」地笑起来。笑毕,她问道:「你能竖起来吗?」我又点点头。半天没有声音,我偷眼看她,发现她正看我,有些不相信的样子。
狗摇着尾巴跑出去了,我站起来向凹坡上看去,奶奶迈着小碎步正往下走来。
姐姐也看见了,给我说:「记住啊,不要说,要不然不理你。」奶奶在门口看见旱烟把子,我只抽了半根,烟把子一般不扔,都装起来,弄碎和在烟里继续卷,那个肯定不是我扔的。但奶奶就看我,我急了说碎哥前面过来了。姐姐在奶奶身后给我猛使眼色,我知道露嘴了,结巴着不知道说什么。姐姐编慌说:「他来借煤油,我没给,就走了」。晚上奶奶进去给大妈家还钱,姐姐拉我到牲口窑里,又掐又拧,说我是故意的。我解释不是,是忘记了,她就脱了裤子,让我弄她,说我弄了就不故意了。
我抱了些干草放在门槛里,她说这里能听到外面,万一奶奶回来就知道。我脱了裤子爬上去,但牛牛没有竖起来。姐姐说我不行,没长大,不要再弄了。我说想摸她奶头,她不同意,说我手脏,弄脏了她衣服。我喜欢她的奶头,就结巴着央求,最后她掀起来让我摸。手刚搭上,感觉牛牛就大了,往她交裆里钻。
姐姐感觉到我牛牛大了,就想把我压着的腿抽出来,可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反倒骑着往她腿缝里顶。她骂我,说我蠢的要死,使劲拧我胳膊上的肉。我疼地跳起来,才发现她叉开了腿,招手叫我爬上去。
她把手伸到下面,抓住我的牛牛对准一个地方,拉我屁股让我叠。我很着急,心跳的厉害,但怕她没有洞洞,弄疼她。她不耐烦的很,用两只手抱住我屁股往下拉,一下就把牛牛弄进她疲里。里面就像个鸡窝,热呼呼的,舒服的很。她让我抬屁股上下动,我照做,越加舒服,连续这样着,牛牛就摩擦地发疼。想取出来,但还舒服着,又舍不得,便忍着疼继续那样弄。姐姐哼哼着,我问她,她说是舒服地哼哼。于是我也学碎哥的话说:「美不美?」她说:「美」,就感觉她抱我抱得更紧了。
突然,牛牛头那儿,就是尿尿的地方,猛的一阵剧疼,好象皮被撕破了。我想爬起来,但她抱着我腰,起不来,屁股后面又开始抽动,一跳一跳地往里面冒尿。
我喊:「我尿里面了,快松开」,她也感觉到了,但不松,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等我尿完。
离开她后,我对着外面的光线看,牛牛的包皮被翻到后面,发红的头头完全露在外面,似乎有些肿,我想可能叠活了就变成这样了。姐姐穿裤子,穿好就打我,边打边拧,说我冒她里面,要怀小孩就让奶奶打死我。我赶紧跑出院子,远远地蹲着看。夜色已经降下来,远处的山峦开始模糊起来。
【完】